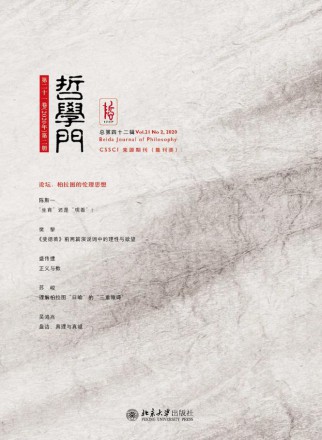哲学人生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18:11:42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哲学人生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哲学家尝谓:“以常识非哲学,疑若可笑,实则哲学之穿凿迷障,正当以常识正之耳。”[6]719面对在中西方哲学中自来便成立说绕不开之根本话题的“善”,刘先生却举重若轻地以一“生”字准之。初看来,似乎题不对义,也无奇特深刻之感。然而,这位“神童”加“天才”的旷世奇才从来出手不凡,他的“常识”是通达“神奇”而为言的。他虽一边言“夫平常神奇者,相对之词,宇宙固如是,即平常,即神奇,本无分别,特以人间所见有常有罕,遂以较罕者为奇耳”[6]737,可也不得不承认“此固非深探人生而推本宇宙无以言之也”[5]263。刘咸炘先生说:凡人之所以学问思辨者,无非求善,而天下之难辨者,则无过于善。善者价值之词,价值必有标准。审天下之所谓善不善者,固不以生为标准。杀人为不善,以其伤人之生也;欲为不善,以其戕己之生也。或谓全己之生非善,全人之生乃为善,则试问全人之生何以为善?岂非以人皆欲全其生乎?其他所谓善不善,莫不如此。故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也。夫如是,则人既生矣,即既善矣,何乎斤斤然讲道术乎?斤斤然讲道术者,求善其生也。既曰求善其生,则是生有善有不善矣。与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之言毋乃太相谬乎?曰:非相谬也。凡所谓生之不善者,浅见者以为生耳,实善不生也。杀人者人必杀之,欲全己生而终害己生也。人自以为尽生人之乐,而不知漏脯救饥,暂饱而终死也。是故生有尽不尽而以久为善,善之准在生而尤在久生,久即善,不久即不善。[6]638由此,刘咸炘先生认为,善的根本义准在生,而生的根本保障也正在于善。一方面,“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与此同时,斤斤然讲求道术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明白真正的生唯有依赖决定生否的善作为根本标准。刘咸炘先生进而谓:“善否乃定于生否,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以生。”[6]679《易传》谓“生生之谓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种“生生之德”即《中庸》所谓“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之“天德”,或许也正是《卫灵公篇》中孔子告诉子路的“由!知德者鲜矣”所指之“德”。在刘咸炘先生看来,此“德”或“天德”无疑为至诚纯善之道体,因此,人以纯善而成全其生,通达天人一贯并非玄幻。天道之德乃生乃善,因此说“善之准在生”,“善否乃定于生否”。此也正证成“生即善”,故刘咸炘先生谓:“儒者所证得者,止此生生之机。”[6]790不仅如此,刘咸炘先生还引证西方学者亦有相同之见。如他说:“法人戴森柏作《自然道德》一书,作善之定义曰:所谓善,乃足资保全与扩大生命之任何事物,乃谓促助个人与其所隶社群和谐伸张之任何事物。”[6]682此外,刘先生还认为除却高深之哲人,就是像斯宾塞这般主进化论者,也不得不以“最高之行为,乃引致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者也”[6]682为准,也不得不以人生为善准。因此,刘咸炘先生指出:“以完成生之本身为善之本,非新说也,乃古今中外深达之贤哲所同主。”
二、人生鹄的
篇2
二、“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
仅仅找到乱世之中通向生存的第一把钥匙还不够,还必须有第二把钥匙。“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便是庄子所找到的第二把钥匙。这把钥匙是从楚国贵族叶公子高和鲁国贤大夫颜阖的经历中找到的。叶公子高要被楚王派去出使齐国,但齐国对待使者的态度一向是“甚敬而不急”,因此他担心此次的使命如果不能够完成的话,“则必有人道之患”,如果此次的使命能够完成的话,“则必有阴阳之患”。而且他早上接受了使命以后,晚上就饮起了冰来,可能已患上了内热症了。他担负的使命刚刚开了个头,就已经有了阴阳之患。他已经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无论使命能否完成,他都将会有灾祸,但孔子在接下来的话中,还是为叶公子高找到了一把打开生存之门的钥匙。针对叶公子高的情况,孔子首先劝导他说,人生于天地之间,事亲与事君是无可逃脱的责任。对于事亲来说,只要“不择地而安之”,也就是不论身处何地,只要能把父母安顿好即可。这对于叶公子高来说自然不需费太多的事情即可办好。而事君,则要“不择事而安之”,也就是不论什么事都要为他办妥,才称得上“忠之盛也”,这就对臣子是一个极严峻的考验,如眼下叶公子高就遇到了这样一个考验,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庄子又借孔子之口对他说,要做到“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孔子告诉叶公子高,既然这是为人臣子的固不得已的事,那么就应该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似乎与前面孔子劝颜回的态度不太一致。其实不然,颜回游说卫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叶公子高则是无可逃脱的。孔子在为叶公子高分析了外交中的“溢美”、“溢恶”的严重后果之后,以“法言”的形式向叶公子高指出了外交的原则是“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然后又分析了外交中凭借智巧角力时出现的“阴与阳”、“治与乱”、“谅与鄙”、“简与巨”等复杂状况,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奇巧”、“奇乐”的结局,最后仍然以法言的形式告诉叶公子高在外交中一定要做到“无迁令、无劝成”。告诉完叶公子高这些以后,庄子将这些生存哲学精辟地概括为:“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而且还说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就是“至矣”,也就是相当完美了。这实在令我们为他拍案叫绝,正是在这种生存哲学的指导下,庄子为当时的一大批伴君如伴虎的官僚贵族们又找到了一把打开生存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适合鲁国贤大夫颜阖。颜阖将要成为卫灵公太子的师傅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但是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要傅的这位太子的品性是“其德天杀”[,而他的智慧正好能够识别出别人的过失,而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如果对他不讲究治国原则的话,就会危害卫国,而如果对他讲究治国原则的话,又会危害自身的生命。颜阖应该怎么做呢?庄子这一次则借蘧伯玉之口提供给他的生存哲学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也就是说让颜阖外表上最好多接近卫灵公太子,内心里最好多顺从他。即使这样,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还应该做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也就是外表上接近他时又不要过分陷进去,内心里顺从他时又不要太显露,要做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涯”[,这样就可以做到“达之,入于无疵”[的境界,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蘧伯玉对颜阖的这番教导,不正是庄子借蘧伯玉之口对“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生存哲学的生动阐释吗?为了能更清楚地表达这一生存哲学,庄子接下来又连用了三则寓言来进一步阐述:螳螂因“积伐而美”而怒其臂挡车的不智之举;老虎虽然凶猛,但因为养虎者能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因而它不得不乖乖地向饲养自己的人献媚讨好;而养马者因为马身上有“蚊虻仆缘”,但他由于“拊之不时”而终于导致了马“缺衔毁首碎胸”的严重后果,这三个例子,两反一正,进一步说明了在利用“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这把打开通向生存之门的钥匙时所要把握好度的重要性。
三、树立“无用致福,有用招祸”的生存观念
篇3
陈硕
指导教师:黎英
福建省南平市滨江中路447号A座904#室
35300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明亮的灯光下,我轻吟着《论语》。精炼的语句琅琅上口,它象一支美妙的乐曲使我沉醉其中……。
初识《论语》是在新华书店里,吸引我的是古香古色的封面。无意间,看到其中的内容,虽然读起来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那有着独特韵味的句子,令我感觉到里面蕴涵了不少的哲理。买回家后,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虽然有译文的帮助,但我仍觉得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含义。
与《论语》结为良伴,是在六年级上学期,老师要求我们背诵三章节的《论语》。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论语》的‘魅力’何在?,为什么连老师也要求我们背诵?”。带着这些大大小小的问号,我又拿出了“尘封已久”的《论语》,并制定了一张计划表,每天不要多背,一页就可以了。重要的是领悟其中的奥妙。于是,每天清晨,我家的阳台上就多了一个小女孩大声背诵《论语》的身影。时间一长,我便发现《论语》中的句子十分简洁明了,而且表达的中心思想都十分突出,令人深思。
篇4
一、创作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使世界文坛越来越多的作家焦虑不安。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思考这一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前苏联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艾特玛托夫于1970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白轮船》,这是一部在人与大自然主题中充分渗透道德哲学内涵的作品。该小说自然情节的描述并不复杂,但在描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却让伦理道德思想得以深刻的体现,被认为是作家的巅峰之作。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被遗弃在外公家的七岁孤儿,没有名字。孩子喜欢到山顶上眺望碧蓝的伊塞克湖,寻找一艘游弋在湖面上的白轮船。他听说爸爸是水手,于是他渴望变成一条鱼游到湖水里,上船扑向爸爸的怀抱。外祖父给他讲长角鹿妈妈的故事,那是个动人的传说:长角鹿拯救过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但后来鹿妈妈的后代遭了殃,成群的鹿被杀害了。从此,这个地方再没人看见过鹿。小男孩牢牢记住了这个故事。有一次小男孩突然看见了两头小鹿和一头白色母鹿,他好像在梦中,一口气跑回家,告诉了外公。可是,第二天,正当小男孩昏睡时,一声枪响把他惊醒,他看见大人们忙里忙外,孩子在棚子里看见兽皮和鲜血,再看墙根下带角的鹿头,他浑身冰凉、毛骨悚然。他听见可怕的笑声,觉得有人拿斧子对准他的眼睛,他惊恐地拼命躲闪。谁也没注意,孩子摇摇摆摆走到河边,跨进水里,去寻找他梦中的长角鹿妈妈和白轮船去了。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起人们维护真理、保护自然的良知。
二、生态文学的特点
生态文学是当代文学与生态思潮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把关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它以人与自然为主题,以关注人类生存环境为起点,从道德与精神方面探索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新内涵,来唤起人们珍惜我们的家园――地球。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生态文学专家。当人类生存遇到困境和大自然遇到生态危机时,他哲理性地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艾特玛托夫在1985年2月17日第七期的《莫斯科新闻报》答记者问中曾说过:“四十年来,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条件。于是,有些人便自我陶醉,丧失了记忆,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而不追求精神享受。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才是使他配得上活在地球上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心安理得地拼命追求升官发财,一味伪善,首先要使自己不能称之为人,就像我这部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那样。眼前的利益不应夺去我们的记忆。因为记忆是我们铁面无私的良心。而良心是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背叛他精神上的最高理想的。”作家认为,人与大自然应当具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人们应该抛弃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大自然平等、和平相处,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人类社会,这正是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得以生存。艾特玛托夫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内涵及关系。这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挑战,使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能够觉醒,表现出一种超前的生态观。艾特玛托夫通过《白轮船》这部小说,反映了20世纪以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同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即人类不仅应该对自己负责,还应对地球负责,同时还得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类必将毁灭自身。
艾特玛托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
艾特玛托夫说过:“我越来越相信,小说的哲理性比重应尽可能增加,如果哲理性的比重小,而以主题的迫切性取胜,那么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就会失去意义。”不难看出,作家非常注重哲理探索,经过长期探索得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沧海一粟,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说,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附属于自然。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是自然之子,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平等相处。
艾特玛托夫非常热爱大自然, 深刻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 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他说:“热爱大自然和必须保护大自然的题材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 事实确实如此,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生存,开始对大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包括污染环境、无序地残杀稀有动物、乱砍滥伐,所有这些行为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艾特玛托夫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他在《白轮船》中涉及了这一主题,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从人是大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
一、人是大自然之子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 ,“我们连同我们自己的头脑、血和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作者得出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共赢和共荣的关系,而不是征服、改造和索取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既然是伙伴关系、朋友关系,那么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尊重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克服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思想,树立人与大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艾特玛托夫向来反对“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征服者”与“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反对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一切行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人应把森林当做“绿色的朋友”, 把动物视为“人类的小兄弟”,这才算得上是 “自然之子”。
在小说《白轮船》中,当孩子惊喜地发现了三头梅花鹿的时候,鹿也同时发现了孩子,但它却却并没有害怕,“这头长角鹿妈妈细心而安详地朝孩子望着,好像在回忆:它在哪见过这个大脑袋、大耳朵的孩子的……小鹿肥敦敦的,又结实又招人喜欢。它忽然又抛开柳条儿,活跃地跳了起来,拿肩膀去蹭母鹿,围着母鹿转了一会儿,开始撒娇了,拿它那还没长角的头使劲地擦鹿妈妈的两侧。长角鹿妈妈静静地望着孩子。”
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生态美景,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和谐友好地共处着。这正是作家殚精竭虑的东西,也是他内心世界的流露。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始终把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认为是主仆关系,始终没有超出这个想法。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就是把人类自己同自然界分割开,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以统治者自居,却忘记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界的婴儿;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仆人,就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一无是处,面对自然侵害时逆来顺受,这也是不合常规的。从世界文明史来看,这些思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层面,从思维上进行理性的探讨。要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必须抛弃旧观念,注入时展的新内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呢?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自然界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的关系,更不是“我们是主人、自然界是仆人”的关系,而是人类是自然之子。所以我们应该放下主人的傲态,放下仆人的卑态,平等地与大自然进行对话,理性地与大自然握手,与大自然共谋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才会越来越美好,人类的生活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
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
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顺应自然。因为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人类由于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自然而频频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当前人类的居住环境日趋恶劣,都是因为人类违反大自然的规律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平衡,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而掠夺大自然、残杀万物生灵、毁坏大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破坏平衡的过程,也是人性道德堕落、变异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残忍、贪婪、自私、冷酷、功利主义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蜕变和精神的堕落。艾特玛托夫把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同人道主义、人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是否尊重大自然当做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善恶与否的标准,并把不同的人们之间因为不同的观念而引发的冲突归纳到善恶冲突的范围。
《白轮船》中描写了善和恶两类人。莫蒙爷爷和孩子是善良人的代表,他们不仅对人友善, 对自然也是和善的。莫蒙爷爷是护林所唯一一个尽心尽力看管森林的人,他说:“看管森林的人,就是不让树林受到任何损失。”他相信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把白色长角鹿妈妈看成是吉尔吉斯民族唯一的恩人和母亲,对她敬若神灵。《白轮船》中的小男孩也热爱大自然,在林中虽没有小伙伴儿与他玩,但是他并不孤独,因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朋友,吉尔吉斯古老的长角鹿母的传说滋润着他的心灵。莫蒙和小男孩儿都是与自然亲和为善的代表,是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明,正因这一点,人类才优越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
在小说《白轮船》中,护林所的领导奥罗兹库尔谋取私利,偷伐森林。当树林中突然跑出三头美丽的梅花鹿时,善恶两类人的态度完全相反。莫蒙爷爷和小孩尽力想为长角鹿妈妈的后代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护林所领导奥罗兹库尔等人只看到鲜嫩的鹿肉和硕大的鹿角。鹿的出现,瞬间将两类人分为善恶两类。艾特玛托夫把对待大自然中动物和植物的不同方式和不同态度,作为判断人类善与恶的标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每种动物的悲惨遭遇最后都以人的悲剧为结局。《白轮船》中三头梅花鹿的死让莫蒙爷爷非常痛苦;而纯洁天真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河边,直接跳进了水里。 就连残酷屠杀梅花鹿的奥罗兹库尔,最终也没有落下好下场。他的这种行为远不止他一人所为,他只是作家塑造的“恶”的形象代表。他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始祖、对自然的背叛和对传统道德的否定,又是“对神话传说的轻蔑,也是对千百年传统精神财富的弃绝”。
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
艾特玛托夫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了更深刻的揭示,从人是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意义。同时,作者也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白轮船》提到科克泰的贪婪、奥罗兹库尔的虚荣与傲慢。他还强调:“贪财、权欲和虚荣心使人苦不堪言,这是大众意识的三根支柱,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支持着毫不动摇的庸人世界。大大小小的罪恶都藏匿于这个世界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人世间善与恶,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些最平淡无奇的事物中”,但是,“为什么总是恶战胜善呢?”这才是艾特玛托夫思考的主要内容。它总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在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的善与恶的冲突、对抗中,总是把人的善恶与保护大自然联系起来。因此维护人与大自然的统一和谐,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间的真善美!艾特玛托夫认为,要想根除破坏大自然、虐杀生灵、掠夺自然资源的恶行,就必须树立人们心中的善意,只有善意根深蒂固,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大自然才会得到保护,人类才不会面临道德沦丧所带来的威胁。否则,人类将“由于自己的暴虐而毁掉这暴虐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韩捷进.艾特玛托夫[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0.
[2]胡志文.生态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土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