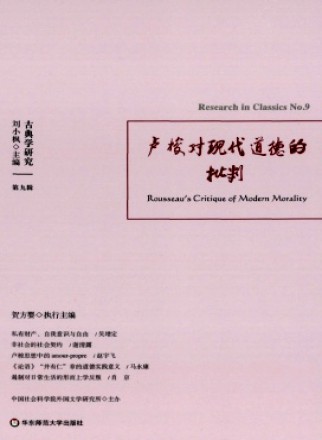古典文学知识范文
时间:2023-05-17 10:16:49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古典文学知识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凤凰出版社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32开
国际刊号:1006-9917
国内刊号:32-1101/I
邮发代号:28-3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6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篇2
那么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为什么是古典时代呢?当我拿到四箱书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首先这个数量让我感到吃惊。当然,网络时代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不足为奇了,我知道一些网络签约作家,他们几乎是每天要往网络上贴将近1万字,必须有1万字的容量才会增加他的点击率,这样的高产他们自己也叫做灌水。但是王丕震的高产,我想如果是跟灌水对应的话,他应该是注油,注进去的是油,油是可以燃烧的。所以我想王丕震他的意义绝对不在于数量。
我在翻阅王丕震的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与王丕震相类似的台湾作家,叫高阳,他也是专门从事历史小说写作的,其实高阳也是属于古典时代的,古典时代的文化市场,他也是产量很高,但是有一点高阳无法和王丕震相比的,王丕震是在晚年,18年的时间出现一个“井喷”,这18年写了142部书稿,高阳一共写了90余部,有105册,但他是从1951年开始专门从事写作,写了40来年,高阳的书在大陆几乎都出齐了。有个出版社主编当时说,中国大陆有11亿人口,也没有出过一个高阳。现在看来其实他说错了,至少他没去关注云南,在云南的丽江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王丕震在这样写作。
我为什么说他是古典时代最后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呢?我觉得他的历史小说写作有其独特性,我把他的历史小说看作是知识审美的历史小说,他不同于当代文学流行的那种借古讽今的思维,实际上中国从新时期以后,基本上还是这种借古讽今的思维,即写历史人物,要把今天的观点放到这个历史人物中间,放在历史事件中间,把对现实的思考移入到历史中间去,基本上是这样的思维。而王丕震的小说是纯粹的、知识审美的历史小说,我觉得是缺乏市场,没有培育起这样的市场。我很赞成李建军说的一个词,就是王丕震的小说具有典雅性。
篇3
中国是诗的国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些作品以广阔的思维空间,隐含了许多富有哲理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诗词给后人以启迪和思考,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加强古典诗词教学,培养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应成为高职语文教育的重点。然而,在当前古典诗词教学中,却存在着重理性而轻感受的倾向,教师只管按部就班地讲解作者生平简历、主要事迹、思想倾向以至课文主题思想及艺术手法等,而学生对诗词的意象、诗人形象的理解无法在心目中鲜活起来,更不要说对诗词的更深层次的把握了。在古典诗词教学中,教师如何给予正确的引导,提高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发挥其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作为高职语文教师,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和提高。
一、明确诗词体现的人文关怀,培养学生人文素质
语言教学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人文素质培养。语文本身决非是单一的一种工具,还有育人功能,是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之一,人文精神是语言的基本属性。在这方面古典诗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曾激励多少炎黄子孙为中华崛起而不断探求真理;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流露真挚质朴的朋友之情成为人们称道传颂的佳句;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了作者普济众生的阔达襟怀,感触至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铮铮誓言何等洒脱痛快,着实令当今的某一些当权者汗颜;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吟出了普通而崇高的母爱,成为千古绝唱;李清照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气概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的浩然正气,曾激励多少中华儿女面对,威武不屈,视死如归。所有这些古诗词渗透了一定的人情美、人性美和爱国主义思想,有利于教育学生面对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某些社会现实,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洁身自爱,健康发展。学白、杜甫的诗歌不但使他们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表达的思想感情,讴歌爱国主义等丰富内容;而且还可以领略到李白雄奇奔放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杜甫沉郁的创作风格,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学习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可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修养,让他们受教于潜移默化之中,得益于身心愉悦之时,对学生的整体素质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鉴赏水平
“诗是中国文学美学特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作者的情感体验,渗透着诗人崇高的审美理想和新颖的审美情趣。在古诗词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审美角度,培养提高提高学生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
1.引领学生领会古典诗词蕴含的真情美
真情美。艺术中的情要真,真情才能铸真景,真挚浓烈的感情来源于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感受,是积淀着人生哲理和生活意蕴的审美感情,古人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只有客观事物使作家“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诗品》)这时候才会有好诗诞生。李后主的《虞美人》被众多词评论家推崇备至。“春花秋月”,多么温馨和富有诗意的季节啊,但诗人却丝毫无留恋之心,“何时了”,怎么还不结束呢!诗人之所以如此悲观和绝望是因为南唐灭亡了,诗人不再是南唐君主,而成了别人的阶下囚。“雕栏玉砌”虽然还在,但已物是人非,“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艺术的表现手段上看这属于比喻,事实上,这不正是诗人内心情感的真实表现吗?许多人喜爱李后主的这首词,主要原因还是被词中的深沉真挚的情感打动了。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把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自然事物,通过高度艺术概括组成一幅极其凄凉的清秋逆旅图,典型概括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游子感伤之情,诗人在“真”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体验含蓄地烘托出旅人的哀愁,给人以深刻的艺术感染,于是它被称为“秋思之祖”。
2.引领学生感受古典诗词意境美
“意境”即指意与境、情与景、心与物的交溶与统一。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景物只有融入感情,才有生命;感情只有景物附丽,才有依托。创造意境,要化物象为意象,勾勒逼真而鲜明的画面,构成整体性艺术形象。诗词的意境,能够诱发人们的丰富想象,是打开人们心灵的窗户。在诗词这种奇幻的意境中,读者必然同作者一同感受,一同联想,一同思考,一同愤怒,一同欢欣,原来不够明确乃至没有认识的生活哲理会得到展示,原来不甚清晰或无法表达的情感能得到抒发,读者从中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满足。因此,引领学生真实感受诗词意境之美,诗人形象就会在学生心目中生动起来,诗词的内涵和精髓也就很容易领悟和掌握了。
如何具体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进入这种境界呢?古典诗词教学,一定要让学生体会作者的情感。因为,诗必言情,无情不为诗。要走近诗人,与诗人对话,这就要求教师在引导学生体会诗词情感时要达到一定深度。如《寻隐者不遇》一诗语言相当精炼,初读此诗,似觉平易,细加欣赏,则易中有难。寻隐者来去过程,一字未提;与童子会晤时的寒暄和问话,也一概从略;童子答问也当不少,但诗人仅摘三句,答问不多,但寓意深刻。在教学中,教师首先指导学生弄清诗的大概意思和人物,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诗人在松树下问些什么,诗中有没有写?你能根据童子的回答展开联想补充出来吗?”“假如你是书童,你会怎么回答?”然后,教师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这些问话一一作答,并让学生分角色当堂进行对话表演。在表演中学生思维活跃,想象丰富,对答如流,还伴有生动、有趣的动作表演,把《寻隐者不遇》中的寻访场面生动地再现出来了,初步领悟到诗的意境。
如学习苏轼的《江城子己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词时,学生对这种中年人生离死别体会不会多深,于是,我们事先叫他们去图书馆借来《朱自清散文集》中《给亡妇》一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朱自清前妻武仲谦生前温柔贤惠、吃苦耐劳的形象及作者的悲痛、思念、歉疚和深深的缅怀之情;通过阅读欣赏,学生体会了夫妻感情的至情深厚,认识了苏轼的词意,进入了情与境谐、以境见志的境界。
3.师生共同品味古典诗词的音律之美
在所有文体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黑格尔说:“至于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章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富丽词藻还更为重要。”诗的节奏是适应舞蹈和吟唱需要而形成的,它是人的生理节奏和生活、自然节奏的统一,人的情感的起伏、波动和生活节奏的张驰决定了诗的节奏。古典诗词之美,首先在于她于的音律之美。读起来琅琅上口,优美动听,所以,教学古典诗词师生必先吟诵。吟诵不可停留在一般的教师范读、个人吟读、集体齐读等浅层次上,而是要在理解诗意词意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诗词的语言美,特别是音律美。在这种美的熏陶下,再发自内心地美美地吟诵,直至见诗意词意之美及诗人词人志趣所在。我国《诗经》中所描写的“砍砍伐檀兮”正是伐木的节奏,李白的《蜀道难》“噫吁哦!危乎高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可以通过节奏起伏发现诗中所包含的起伏的感情,《蜀道难》开头突兀沉雄,显然表现的是见蜀道高危的惊惧情绪。全篇节奏较慢,起伏不平,通过节奏的变化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至于李清照的《声声慢》连用七对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则更是千古绝唱,它把诗歌的音乐性与诗人的内在情感相融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人内在情感的流动。这首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因为它有着动人的节奏和旋律,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优美的节奏和旋律恰当而又充分地表现诗人孤独、空虚、悲苦、凄凉的精神状态。“寻寻觅觅”写词人的心情寂寞,似有所失,茫然寻觅精神慰藉的心理情态。而寻觅的结果呢?依然是室空无人,一片冷清。“凄凄惨惨戚戚”进一步写诗人忧愁悲伤。因此,从词的外形来看,叠字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效果,而从词章所表现的情感内容来看,这短促而抑郁的声调传达的正是词人凄凉悲苦的心绪,情景交融,回味悠长。
三、培养形象思维,提高想象力
诗是用语言向读者的想象力提供形象的,因此,诗的语言凝炼、生动、含蓄。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短短二十个字,却有人物、有环境、有情节,经过几问几答,诗人想找到“隐者”的迫切心情和童子自然之至的答话神态毕现于读者眼前,而那位与青松、白云为伴,以采药为乐的隐者的形象令人遐想不已。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只用了两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不仅凝炼,而且给人以极其鲜明的形象感。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诗人总是凭借诗歌中的形象来抒发感情的。如古诗词中的“菊”、“松”、“春花”、“明月”等根据诗中的形象,依靠自己的生活感知和想象力去体味其中的情感。黑格尔说:“如果说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美学》)高尔基也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家的想象应该是飞腾的,跳跃的。诗人王维的诗,正如苏轼所说的那样,确实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展现了一幅气势磅礴,造化自然的山水画卷。在这里,诗人的想象是飞腾的,一个“外”字,把这一巨幅画卷的空间拉向了无限的远方,创造了一个“黄河之水天上来”、“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画境;而山色的那种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情景,又颇有点象印象画派的描绘,从郁郁葱葱的朦胧山色中给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而又超然物外的感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短短十个字紧紧抓住事物的形象特征,跃然纸上的是一派莽莽平沙、浊水斜阳的塞外风光。这种诗情画意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联想和再创造余地。总之,依据诗中的形象,通过想象我们也就能在有限的篇幅里领略到无限宽广的艺术内容。
四、借用现代时尚元素理解古典诗词
为了更好地教学古典诗词,还可以借用现代时尚等元素来帮助学生理解古典诗词,深化他们的认识。现在,有很多歌词都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像《月满西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学生都很熟悉。这里,对于学生,背诵已不在话下,怎样适时增进学生对诗词情感的理解才是重点。这时,可先引导学生体会歌曲的旋律,因为如怨如诉的音乐与原作中忧伤而旷达的意蕴往往具有相得益彰的效果,学生会在这种感性的自己喜欢的氛围中深化对原作诗词学习的认识。如在教学古诗《上邪》时,可请学生回顾电视剧《还珠格格》中的主题曲《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得知这首歌词原来由改编古典诗词而来,他们非常兴奋,课堂讨论非常活跃,这使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更浓了,理解更深了,教学效果自然也更好了。
“诗言志,歌缘情”。从这个角度说,古今诗歌始终都在表达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我们完全可以把领会现代诗歌作为古典诗词教学的一个补充,拉近学生与古典诗词的距离,从而加深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如讲授上述李白诗作时,就可先介绍余光中诗《寻李白》中“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等句,余光中用形象的语言、精当的议论,表达了李白的个性特征与人生价值。先介绍这首诗给学生,可能比单纯介绍李白其诗要有趣多了,效果也会好得多。
综上所述,高职语文学科古典诗词的教学,既要从学科特点出发,使之具有一定的文体性。又要从以上几个方面提高学生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如此,才能强化古典诗词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热爱中国古代文化,在人文教育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古典文学名著被制作成影视作品。近年来,我国又兴起了一股古典文学名著影视作品重新制作的热潮,在制作过程中都把重心放在了创新、超越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上。影视制作包括编剧和拍摄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语言内部的转换过程,目的在于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重构原作意义;第二个过程是符号之间的转换过程,是通过声音、图像等媒体手段对剧本内容进行多模态构建。这两个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广义的翻译行为。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古典文学名著的影视制作也是对原作的改写。本文试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为例,分析文学作品影视制作过程中改写思想的体现。
二、改写理论与影视制作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接受环境中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操控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写。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改写都体现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行为,而且也体现赞助人的意志。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权势地位。作为一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赞助人利用话语权力对译者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甚至对整个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而译者是以改写者的身份参与翻译活动的。但是,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之下,译者也并非毫无选择,相反,他们可以选择接受制约,也可以选择挑战,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体现译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主体性既包括译者的能动性,同时也包括译者的受动性。译者受到的制约越多,其创造性也越强。
改写思想也体现在古典文学名著的影视制作当中。译者即影视制作者,赞助人即投资者和潜在的观众等。他们对影视制作的操控也体现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权势地位等三个方面。影视制作者不但受到赞助人的操控,同时也受到原作的束缚。和译者一样,影视制作者只不过是从两个枷锁中间寻求一条出路,实现一种平衡。理想的状态是最后的作品既能体现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保障译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同时又不违反原作的思想精神。这就要求影视制作者在赞助人意志的操控之下,选择适当的策略和方法,在忠实于原作思想的前提下对原作进行改写,使影视观众与原作读者有着相同的阅读享受。
三、影视制作中的改写
原作的思想通常隐含在情节的描写中,或者被物化在主要人物形象上。《水浒传》中的宋江仗义疏财,被誉为“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然而,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其貌不扬的宋江为何能够服众,做梁山之主呢?有研究认为,宋江从上梁山泊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具有军事家的机智和谋略。事实上,宋江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既要反抗朝政的腐败,又要维护帝王的统治。作者试图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希望把宋江塑造成忠义双全的楷模,同时,深受儒家“无为”、“寡为”思想影响的作者不可能让宋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这也使得宋江的形象长期以来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
作者对宋江形象的刻画中采取了科学叙述和艺术叙述两种叙述方法。按照科学叙述,宋江是典型的仁义之士;按照艺术叙述,宋江所做的都是不仁不义之事。影视制作者应该把这一矛盾忠实地表现出来,对原作的改写既不凸显宋江的仁义道德,又不渲染宋江的“勇悍狂侠”。下面分别从人物形象和水浒精神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在影视制作中的改写。
1 人物形象的改写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影视作品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原生态的,等待着读者去解读,“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后者是由影视制作者创造出来的,已经经过了解读,给观众留下的解读空间很小。杰出的编剧或导演能够从一千个哈姆雷特中抓住最为典型的一个,使之成为最大概率形象,或者尽可能地使其保持原生状态,留给观众较大的解读空间。经典名著能够让读者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理解和新收获,因而百看不厌。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有时也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受,那些导致人们百看不厌的成分恰好是没有被制作者完全解读的部分。优秀的影视作品会诱发观众阅读原作的兴趣,拙劣的影视作品会限制观众做进一步的思考。
《水浒传》第六十回讲述晁盖率军攻打曾头市,半夜三更劫寨时中了埋伏,混乱之中被一枝刻有“史文恭”字样的毒箭射中面门。作者没有明说是史文恭所射,但读者从箭上所刻之字上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史文恭所射。而晁盖临死时对宋江的嘱咐“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却意味深长。其一,晁盖知道宋江有投降朝廷的愿望,不希望把寨主的位子让给他,他量宋江才能平庸,不可能捉得“射死我的”;其二,“射死我的”没有明指,说明晁盖知道射死他的人可能不是史文恭。原作的叙述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金圣叹的解读是:杀害晁盖的其实并不是史文恭,而是宋江。隐含在文字当中的这些微妙信息在电视剧《水浒传》和《新水浒传》中都被抹杀得干干净净,用特写镜头直接把射杀晁盖的凶手推向了史文恭,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思考的空间,其艺术价值也大大削弱。
原作对宋江形象的刻画集中体现在骗取秦明做强盗和逼迫朱仝上梁山两个片段中。在《水浒传》第三十四回,秦明被花荣用计活捉。为了让秦明上山做强盗,宋江派人去青州城杀人放火。导致秦明全家被杀。
秦明见问,怒气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
按理说,宋江正是那“该剐的贼”。然而,秦明“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这种反应显然与秦明性情不符。在描写秦明的几段文字中,作者四次提到“秦明是个性急的人”。如此性急之人,如今也“只得纳了这口气”。这个闪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宋江这么做只是为了“先绝了总管归路”。然而,在宋江自己仓卒决定并走上梁山泊的途中,一封报丧的家书,便使他叫苦不迭,捶胸顿足,哭骂自己是不孝逆子。这种作为似与仁义无半点瓜葛,而宋江表现出来的不可动摇的孝心正体现了他自私阴险的本性。
这段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关键作用的叙述在电视剧《水浒传》中被一概抹去,在电视剧《新水浒传》中虽然得以保留,但对原作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写:一是王矮虎、刘唐等在宋江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去青州城杀人放火;二是青州知府以为杀人放火者是秦明,于是杀了他全家作为惩罚。前者直接把罪行从宋江身上移开,并成功地加在了慕容知府的头上;后者阻断了观众的解读渴求,并引导观众表达对残暴官吏的愤怒,对秦明弃暗投明的喝彩,对宋江“替天行道”的支持。这种改写表面上维护了宋江忠孝仁义的形象,但实际上却打破了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试图寻求的平衡,使观众对宋江的形象产生认识上的偏移,从原作、作者和读者的角度来看都是失败的。
《水浒传》的主题之一是逼上梁山,但实际上大多是宋江所逼。宋江上梁山之后,“众好汉皆宋江延揽而至”。在《水浒传》第五十一回,虽然“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但真正的仁德却从朱仝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朱仝为了雷横能够照顾老母而私下放了雷横,替他吃官司,赔尽自己家私,被发配沧州。因为深得沧州知府喜爱,朱仝在盂兰盆节带知府的小衙内看灯,却遇到宋江唆使来逼他入伙的雷横。
雷横道:“哥哥在此,无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延自误。”朱仝道:“兄弟,你是甚么言语?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
然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宋江指使杀人成性的李遣残忍地杀害了小衙内,又绝了朱仝的归路。
只见吴用、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望着朱仝便拜,说道:“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朱仝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
当下朱全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
按理说,朱仝与宋江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这种仇恨也只在李逵碍于宋江情面,“只得撇了双斧,拜了朱仝两拜”中化解了。朱仝的仁义与宋江的不仁不义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江表面上慷慨大度,但对自己的仇人剖腹挖心,生啖其肉,“真有犬彘不食之恨”。然而,这种典型的刻画人物形象的情节在电视剧《水浒传》中被完全删除,在《新水浒传》中被改写为李逵与朱仝争夺小衙内时失手把小衙内丢下了山崖。虽然保留了情节,但歪曲了原作的意图。
2 水浒精神的改写
文学名著在影视制作中无论如何改写,但不可改写原作的精神。《水浒传》是一部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又浸透着极其绚烂的浪漫主义精神。这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浪漫主义的夸张和渲染集中地体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在对武松打虎的叙述中,武松吃了五斤牛肉,喝了十八碗酒。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这是武松,因此读者愿意接受。尽管是大英雄,武松也未必敢与老虎较量,但在酒力作用下,还是出现了较量的场面。武松本来有烧棒为武器,但如果用武器打死了老虎,也不会在观众心中掀起太大的波澜,李逵后来也曾用武器杀死了四只老虎。作者只好让武松打急了,烧棒打在了枯树上,折为两段,于是只好徒手打虎,“打到五七十拳”,把老虎打死了。这种浪漫夸张的、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叙述让读者能够产生一种冲动和释怀。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电视剧《水浒传》对打虎场面的表现扣人心弦,武松大英雄的形象在徒手打虎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展现;《新水浒传》的制作者显然曲解了烧棒打在枯树上的含义,为了突出场面的惊险、打虎的艰难,在武松与老虎的对峙中,武松明显处于劣势,情急之下伸手捡起地上的石头,随手拔出腰间的尖刀,于是运气使其绝处逢生。武松打虎连烧棒都不用还会用得着石头和尖刀?这显然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压制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观众心目中的梁山好汉,个个英勇了得,人人身怀绝技,七八百斤重的石头能举过头顶,碗口粗细的杨柳能连根拔起,理所当然比一般的市井无赖厉害,一刀杀死牛二,三拳打死镇关西不仅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内。知县看了武松和死虎,心里也自忖“不是这个汉,怎地打得这个虎”。观众岂能接受西门庆能和“这个汉”形成对手?毕竟西门庆不是梁山好汉。然而绝处逢生的场面在武松和西门庆打斗中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