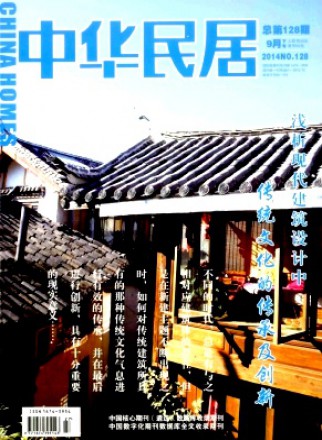雕刻艺术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08-28 09:24:01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雕刻艺术的意义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人们的艺术思维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是人们借以表达自己思想观念、抒发内心情感的具体表现形式。视觉艺术思维是各种表现形式的基础,它综合反映在各种不同的艺术种类及艺术形式之中,反映在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其系统性、严密性、丰富性和强烈的个性。
视觉艺术思维把自然美和艺术美相融合起来,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境界,活跃了人们的情感生活,充实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带给人们新的希望,这就是人类的视觉艺术思维给人类本身带来的美好回报。认真研究我国雕刻艺术的思维表现所给我们带来的艺术启迪应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一。
一、纯拙的艺术思维阶段
中国最为古老的雕刻其视觉艺术思维还处在朦胧迷茫的状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当时所雕刻出的骨器或石器基本上为自然物的利用和粗陋的装饰,而真正的雕塑艺术到新石器中、晚期才开始出现。从大量的考古中发现,雕塑艺术以陶塑和泥塑为主。原始人的生活与渔猎分不开,而渔猎的对象正是种类众多的动物,因此人们视觉艺术思维的特点在于表现大自然中的各类动物,以及人物与动物共同存在的场景。在最为原始的陶器、泥塑作品中,有猪、狗、熊、豹、象、鼠、鸟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动物(图1)。从这些原始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出,原始人类视觉人类艺术的造型与表现手法是简单、稚拙、古朴的,但却很传神,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些动物或人物的表情和神态。如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一个陶制男子头像(图2),头像的造型为陶罐,人面的两只耳朵被塑造成罐子的提耳,表现出原始人在制作此罐时的用心所在。人头上眼睛和嘴都为镂空处理,在眼睛与嘴的上部还隐隐约约可见用墨线画出的眉毛和胡须,表情惊叹夸张,神态栩栩如生。
图1 图2
这几个原始时期的雕像体现出原始人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艺术思维形式,即单纯稚拙的再创作思维,并以艺术造型的手法表现出来。原始人类为生存或为之期待的美好愿望直接反映到作品之中是其生存的必然,也是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二、浑然天成的艺术思维阶段
秦汉两代是中国雕刻艺术界足以自豪的时期,雕塑作品可谓神采飞扬、气势磅礴。从气势沉雄的兵马俑到茂陵汉代大将霍去病陵墓,雕刻风格浑然天成,从气势和写实的陶俑到浑成写意的石雕,都蕴含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趣味,即浑穆、石拙、雄强、俊逸的美学内涵,充分体现了萧何“非令壮丽,无以重威”的思想,成为秦汉艺术宏大气魄的纯正的艺术特征。据史料记载,秦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临洮地区突然来了12个穿着胡服的巨人。秦始皇认为是吉祥之意,便命人按照巨人模样铸造了巨大的铜像站立于阿房宫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铜像胸前还刻有斯所写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据传每个铜像“身高五丈,脚有六尺”,重量达12万千克,这样巨大的青铜塑像在中外雕塑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兵马俑的制造过程中,秦代的艺术家们充分展示了他们视觉艺术思维的活跃和艺术创作的才华,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如果不是平时艺人们将兵士及车马的各种形态、习性韵熟于心,并用艺术的思维形式加以创作变化,进行艺术再现,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完美的艺术水平的。
两汉时期的雕塑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思奇崛,风格豪放,从艺术反映出两汉时期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思想活跃的特点。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雕像是我国雕塑史上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重大创作意义的作品之一。霍去病墓前有立马、卧马、跃马、虎、象、蛙、鱼、野人、怪兽、牛等十多件石刻作品,墓园所有雕塑无一是表现霍去病将军的形象,而是以一尊《马踏匈奴》的雕像记录了将军短暂而闪亮的一生。《马踏匈奴》塑造了一匹雄壮有力的高头骏马,将一个入侵的匈奴踏于蹄下,蜷缩在蹄下惊慌万分、垂死挣扎的匈奴与挺身昂立、坚定沉称的骏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突出了年轻将军的豪迈气概。汉代的艺术家们借用庞大、质朴的巨石材料加以构思,稍加雕琢,寓大巧于稚拙之中,浑然天成,体现出艺术家创作思维的逐渐成熟和提高。
三、成熟的艺术思维阶段
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大量发展石窟雕塑,及至唐代,中国的雕塑艺术已走向成熟与辉煌,其成熟表现在艺术家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上。艺术创作及思维形式集古今中外优秀传统和经验为一体,人们更加注重艺术内涵、艺术本质的表现,创作出大批具有艺术价值的雕塑作品。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石刻浮雕造像就是当时创作艺术思维的典型代表作。石刻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名誉四海,“六骏”造型圆浑精美,各有姿态,或直立、或飞奔,艺术家以其成熟而精妙的技巧塑造骏马的形象,流畅的曲线和略带夸张的处理,使浮雕外观饱满强劲、力度超然,展现出了帝王“君临天下”的统治思想。
中国的雕塑艺术的创作者,本来就有很高的艺术造型水准,他们在保持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外来艺术及印度佛教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有目的的筛选,创造出具有中国本民族特色的佛教雕刻艺术形式。在唐代,许多地方都建造了颇具规模的寺庙石窟,其中有许多佛教雕塑的珍品,体现了佛教大慈大悲、大度为怀的宗教思想和境界。其造像意识既有神秘的一面又有从神秘走向世俗的一面,艺术思维上含有注重表现自然生活中的亲情、美感等内容,并以这种倾向创作出来。
在莫高窟唐代所开凿的200多窟佛教造像中,大都存在男相女性化的倾向。最具代表性的是莫高窟第45窟的一尊彩塑菩萨象,从体态、表情到衣着装扮都是女性的特征,这种男性女相的佛教造像表现出人们思想深处易接受和蔼慈祥、温柔仁爱的形象。将佛教宣扬慈悲和蔼、慈爱体贴的特点渐渐渗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体现出中国人追求阴柔之美的思维内涵,更显示其豁达包容的情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佛教造像逐渐由男性趋向女性化是必然的,也与中国人的审美思维和艺术观相吻合。
另外,对于表现罗汉的塑造,准确地抓住了他们既是凡人,又是得道高僧,具有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这个特点,在创作上刻意表达罗汉们各自不同的神情。从罗汉面部表情来看,人间百态尽显其中:双目凝视、聚精会神,心高气傲、不屑一顾,歪头斜目、放荡不羁,等等。从生活中不同人物瞬间的表情为借鉴来描绘罗汉,突出自然社会中人的情感表现,应用到具体创作中便体现出了思维上已经成熟。
四、结语
雕刻作为我国视觉艺术的主体之一,承载着大量的当代的烙印,是思维信息的重要载体,也是当权者与创作者重要艺术思维体现的实在物,并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审美思想和视觉艺术思维形式。秦代强调写实仿真,气势宏大,帝王之风;魏晋南北朝崇尚宗教文化表现,思想深处蕴含着超世脱俗的风骨;唐代雕刻造型圆浑、气度非凡,体现出民富国强的大发展民风貌;宋代随着思维的转变逐渐走向世俗和平民化,随之也逐渐失去其显赫的风采。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种艺术形式,不仅仅是被雕刻中所具有的先代智慧、高超技艺和巨大的震撼力所吸引,更多的是因为它是精神思维与现实思维最具震撼力的艺术作品,并且给后人具体的思维启迪和艺术创作上的无限遐想。
参考文献:
[1]芦影.视觉传达设计的历史与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蔡凤书.国宝发掘记[M].山东:齐鲁书社,2004.
[3]赵农.中国艺术设计史[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篇2
1 景观环境中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发展
在现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良好的景观环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景观环境为人们提供享受自然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展示城市良好形象,表现人们美好生活场景的平台,是对城市面貌、环境保护、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追求的一种诠释。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古代石雕艺术家们巧夺天工的精美艺术品,是传承和表达历史文化的记载,是人们了解历史,学习进步的有力凭证,更对现代环境景观环境的设计和营造有着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将其运用于现代环境景观设计中,不仅有利于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能够为现代环境景观设计增添色彩。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在景观环境营造中,以其坚不可摧的优势,利用其美观大方的特点,营造个性鲜明、主题突出的景观环境,在现代景观环境的设计中,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运用能够更好地突出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功能性、艺术性等艺术表现力,能够为创造优秀的环境景观设计添砖加瓦,更好地满足功能需求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2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文化内涵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积累和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民族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发生着变化,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民族特色也随本民族历史特征的发展而变化,各民族中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有着各自多种多样的艺术特点,能够很好地反应出一定时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在现代景观环境设计中,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出现,为展现区域民族文化特色,展现区域民族文化精神,有着其独特的、不可代替的艺术价值。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具有丰富的地域性文化内涵。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文化众多,是一个大群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域性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和特点,石质景观雕塑艺术的地域性文化特色非常明显。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地域性文化还存在于各地区的石材和工艺上,由于各个地区的石材在质地、颜色、结构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使用中的方法和形式上也有所不同,也是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素。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区域历史文化也随之变化,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下,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发展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石质景观雕刻艺术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不朽丰碑。在现代景观环境的设计中融入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石质景观雕刻艺术品,能够更好地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树立良好的城市历史文化形象,增强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
3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的设计表达
石质景观雕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鲜明的主题、丰富的文化内涵出现在景观环境中,对景观环境进行装饰与点缀,石质景观雕刻艺术承载着历史赋予它的艺术表现力、承载着历史发展演变的文化内涵,对现代景观环境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篇3
1. 潞王陵神道石像生的研究意义
1.1 潞王陵石雕的雕史学价值
我国古代石雕艺术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劳动人民用智慧鬼斧神工地将雕刻艺术发挥到极致。石雕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又称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指用各种可塑材料(如石膏、树脂、粘土等)或可雕、可刻的硬质材料(如木材、石头、金属、玉块、玛瑙等),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借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理想的艺术。而作为其优秀代表的皇陵石雕,则是以汉白玉和大理石、青石、花岗石、砂石等为材料的帝王陵墓雕刻,由于所雕刻神、人、兽能体现出皇权的威严,加之原材料得诸自然易于长期保存,故成为帝王将相死后极度荣耀的追求。从新时期时代石雕旨在写实的初级阶段到唐代石雕造型丰满、气势宏阔的顶峰时期,最后到逐渐以模仿汉唐代石雕特点的元明清时期,各个历史时期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然而处于明中晚期的潞王陵石雕,能够在追求模仿和浮丽的环境中进行大胆地创意与突破,更显其弥足珍贵。
1.2 潞王陵神道石像生的研究意义
石像生是皇陵或王公贵族墓茔中神道两旁的石雕像,由于它属于地面陵墓雕塑,其规模宏大、成就突出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是皇陵石雕艺术最有力的代表之一。本人所研究的潞王陵,墓穴早已被盗一空,其陵墓石雕也只能谈地上。每一历史时期的皇陵石雕除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之外,也能映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潞王陵修建时正处于明代国力逐渐衰败时期,国库捉襟见肘使定陵时断时续,当面对后金日渐崛起的外患时,还能继续不惜劳民伤财为潞王建造如此超祖制的陵墓,此举岂能不激起民怨?这样看来,我们在研究欣赏潞王陵的建筑艺术和石像生的艺术价值的同时,需要认真思考的艺术之外的政治问题。
2. 潞王陵石像生的艺术价值
2.1 潞王陵石像生艺术的时代意义
由古代帝王墓葬观形成的陵墓特有产物――石像生,本意为“象征生命”,其多寡、种类和品级又成了身份与特权的象征。摆放在潞王陵神道两侧的石像生,以其高大坚实的立体造型,等距离的、左右对称的整齐排列,竭力表达潞王的所谓“仁德睿智”、“泽被四海,恩及域外”等多重寓意,进而突出强化并丰富其中的深刻政治主题。我们透过潞王陵石像生雕塑艺术表象,可以从中悟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创造、追求墓葬形式和墓葬特权的积淀过程。潞王陵石像生的存在价值,不只是烘托皇陵建筑、表达死者生命与权力永恒的痴想,而是能够促进我们研究、整理和开发明代乃至整个皇陵石雕的艺术,无论是对石像生起始的争论还是对石像生作为殉葬替代品演化过程的研探,无论是对历代皇陵石雕艺术风格的发掘还是对石像生艺术价值的探寻,都大有裨益,都会使此类的研探富有弘扬民族文化的时代意义。
2.2 潞王陵石像生的惊世骇俗
潞王陵之所以成为最大的藩王陵墓,是因其最大的特点是逾制,这种逾制除了众所周知的结构、规格和面积,更多地反映于具体设计细节之中。且不说陵前的五供(2个石蜡台、2个石花瓶、1个焚帛炉)都高达5米,比明十三陵高大的多;且不说石牌坊对联 “龙卧太行绵玉,凤栖碧水毖水曜银湟”的“玉”字点故意写高一格,显示比其他藩王的尊贵;且不说高大城墙和庞大建筑群全用石头,号之为“中原石头城”。单说潞王陵的众多龙雕,足以让人感受其中的奇特。正反两面雕刻“潞藩佳城” 的高大石牌坊中,四柱通身雕刻云龙图案,大小额坊正反都有二龙戏珠的浮雕,明间顶部正中雕刻着盘龙,牌坊两侧并列着两座浮雕二龙戏珠图案的石华表。雕有“维岳降灵”的二道牌坊中,除了抱鼓石上8个形态各异的狮子相乐相戏跃然石上外,通体有二龙戏珠石雕图案,尤其是牌坊正中雕刻着盘绕而立的双面龙,一面向南,一面朝北,下有海水相承,龙的面部感情却雕刻得凄楚悲怆。相传潞王无论从长相还是才学,都不比万历皇帝逊色,没有继承皇位自然成为心结,于是太后的娇宠和皇帝的放纵,养成了逾制僭越的霸道,怎奈手无兵权,42岁便因太后去世悲痛之极而撒手人寰,这座龙雕便生动地反映了潞王一生跋扈而又抑郁的复杂心态。不过他的陵墓却使他出尽了风头,这也是他生前始料不及的。
然而,最能表达潞王陵风格特色和雕刻艺术,最能吸引后人研究与观赏的亮点与精粹,最能代表潞王陵乃至整个皇陵石雕水平,则是潞王陵石像生的惊世骇俗。位于牌坊、华表以北有16对翁仲和石兽的石雕群:庄严肃穆、神威异常地排列在神道两侧。这14对石兽和一对文吏、一对控马官,是在传统的狮、麟、象、驼、獬、马石像生的基础上,又特别增加了、爰居、貔貅、豹、狻猊、羊、虎、辟邪诸多石像生,堪称类特数显。石像生排列顺序自南向北,从高到低,分东西两行,依次是、爰居、貔貅、獬、豹、狻猊、羊、虎、狮、辟邪、麒麟、骆驼、象、马,这种排列方式,不仅与其他藩王陵墓不同也异于帝陵。神道石像生在各个朝代特别是明代有严格的规定:帝陵前设置石兽6种,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长陵也都只列狮、麟、象、驼、獬、马6种石兽。潞王作为藩王,陵墓规格必然低于帝陵,但却设置了14种石兽,不仅明显违反祖制,且大大超过了帝陵规格,这在皇陵建筑史上不能不说是奇特。不仅若此,竟然还出现了在历代皇陵石像生罕见的诸如、爰居等石兽,更为潞王陵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使石像生的内涵和寓意更加浓重,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空间。
2.3 潞王陵石像生艺术的整体评价
吸引我们研究和保护的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下的潞王陵,是因为其石雕特别是神道石像生富有独特的艺术价值。造型生动、形象精美的神道石像生,集雕刻技艺、雕塑风格、构思精巧于一体,聚数量多、造型真、外在美诸美之全部,上承皇陵石雕静中有动、威中有严的写实风格,下启石像生丰满优美、气势宏阔的雕塑个性,不愧为中国石雕造型艺术史上的璀璨瑰宝,散发着中华民族传统雕塑文化的独特神韵。其雄浑厚重的雕塑风格,既有汉唐两宋之遗风,又有显示个性风格的创新;其数量多,却个个是雕艺精湛的精品,绝无宋代后期的雕刻粗糙、技艺参差之憾;其形体大,却雕工精细,长短合度,洋溢出构思精巧雕技高超的艺术魅力;其造型真,却达到了近看栩栩如生、远看以假乱真的境界,不仅让研究者叹为观止,亦令观瞻和浏览者恋而忘返。据说曾有马匹路过此地,看到石马以为遇到同辈之骏,便跳跃嘶叫,拼挣缰绳,意欲奔向石马,异类尚且感染如此强烈,何况人乎?无怪众多文人墨客赋诗作词大加赞赏,其中“古殿空山裹,名王有旧莹,秦陵和汉寝,不及此幽情”的诗句则道出了的精华与创新所在。
3. 潞王陵石像生的内涵寓意
潞王陵神道石像生,是传统石雕艺术的精华,也是潞王陵异于历代藩王陵墓的重要标志,而这些狮、麟、象、驼、獬、马之类传统石像生,与那些、爰居、貔、豹、狻猊、羊、虎、辟邪特别增加的石像生,以及仅有文吏与控马官的人物石像生,不仅仅是石雕艺术品,更肩负着特定的寓意,隐藏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
3.1 潞王陵神道石像生寓意及渊源
传统的皇陵石像生一般有以下种类和寓意:大象与人物一对,以取“吉祥”谐音;想象中的禽鸟朱雀一对,带翼四足的动物瑞兽一对,以示尊贵;表示仪仗队伍的鞍马及人物两对,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象征威严;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一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用以保护陵墓。令人惊奇的是,潞王陵牌坊正中那座盘绕而立向南又朝北的双面龙石像生,在历代帝陵中也很罕见。人们都清楚龙自古是皇帝的化身,只有天子才配真龙,而在潞王陵中竟有如此高大的龙石像生,似此绝对违反皇陵墓葬制度的现象却偏偏出现在潞王陵,其生前梦想成帝的寓意和死后成帝成仙的象征便不言自明,不过龙的雕刻所透露出的凄楚悲怆的逼真感情,既表达了潞王生前不得志的郁闷,又凝聚高超的雕刻艺术,为后人雕塑特别是今天的城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潞王陵的其他石像生不仅有传统的象征又有特定的寓意。麒麟是人们想象出来的融鹿、虎、牛、马等形于一体的祥瑞之兽,从南北朝开始皇陵神道列置麒麟这种神兽,以标榜“王者至仁则麒麟出”,而且规定只有帝陵才能置麒麟,以区别于大臣墓前的辟邪,但潞王陵中却兼而有之,何其牛哉?潞王陵神道之麒麟,长宽高等同定陵,具体形象是鹿身、马足、牛尾、圆蹄,通体鳞甲,寓意为“仁得于天下”,这对从来不顾人民群众死活的潞王来说岂非讽刺?唐以后帝陵前列百兽之王―狮子,在象征帝王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尊严的同时,起到护卫和镇墓的作用。潞王陵的石狮,雄健威严,气魄浑厚,根本看不出这个人臣墓与帝陵的区别,倒是表露出工匠借石坯取势,借方取圆,着力体块与线条纹饰之间有机照应的高超艺术。石马及两位控马官合为一组,以此显示潞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石虎与右羊,造型浑实,通身未饰花纹装饰,石羊两角弯于耳下,半跪半卧,取“羊有跪乳之恩”以示潞王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特别是对母后李氏宠爱的感激.这两种石兽无论造型、比例和技法都有宋陵之遗风。一对文吏(潞王没有军队故而没有武将石像生)身着朝服,头戴朝冠,手捧笏板,神情肃穆,以取对潞王的敬畏。从中国雕塑发展整个历程来看,明代陵墓雕刻大体都缺乏生气和力量,表现皇陵石雕的下滑趋势,也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日趋萎靡的精神面貌,而潞王陵石像生雕刻的承前启后轨迹,现实性与理想性、寓意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写实性与装饰性、整体雕塑与局部刻画的协调,以及不同距离、不同角度的视觉触觉艺术效果,可谓独树一帜,既表达了深刻的寓意,又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弥补了明代皇陵石雕的缺憾。
3.2 潞王陵神道石像生的特殊内涵与寓意
潞王陵石像生并非像其他皇陵所表达的普遍意义,而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特有的内涵和寓意。一是掌管军队。潞王自以生前无兵权,不够耀武扬威,于是就有了死后的貔貅石像生,貔貅这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龙头、马身、麟脚,形状似狮子,毛色灰白会飞,经过历代的演变,又成了有独角长尾、凶猛威武形状,有负责天庭巡视阻止妖魔鬼怪、瘟疫疾病扰乱的职责,有嘴巴无吞万物而不泻,招财聚宝只进不出的神通与特异功能,因而人们常用貔貅比作军队,在此以喻潞王军队的强大与威武,善聚天下之宝,在保证潞王挥霍同时足量保障军队供给,可谓寓意深刻。现在很多中国人佩戴貔貅的玉制品也正取其招财进宝之意。二是隐喻龙行天下。潞王生前虽是最大的藩王,但毕竟不是以龙自比的天子,所以石像生除了众多的龙雕以外,还有一般皇陵没有的,该神兽又称为“窳”,传说曾是杀而复活的天神,其外形有人面龙身和龙头虎身等多种说法,但都与龙有关,可惜被名为“危”的神杀死,但后来竟奇迹般地复活,于是便长生不老而位列仙班。由石像生可以看出,潞王不仅要实现当真龙天子的愿望,更有重新复活、长生不老的奢想。三是镇妖除邪。潞王在世时可以说是独霸一方,横行无忌,死后自然怕有人化作厉鬼讨债,于是石像生中便增添了辟邪,据古籍记载“辟邪”是形状似狮、头长独角或双角、身有翅膀的神兽,能除群凶,以其作石像生自然是辟邪祛凶。在汉代它们最受青睐,皇陵石雕中都有天鹿(禄)与辟邪两个石像生,而后代皇陵中都以麒麟代替辟邪,潞王陵中在置麒麟同时又列辟邪,表明陵墓雕刻既崇尚汉唐又试图镇妖除邪的双重寓意,用心何其良苦?怎奈寓意深刻的石像生并没有阻挡住后世盗墓贼的猖獗,潞王的墓穴曾被盗墓贼炸过两次,颇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感慨!然而不管怎么说,石像生的寓意既为皇陵石雕增添了艺术魅力,也为后人雕塑的设计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 期刊:王磊. 凤阳中都皇陵石像生的艺术特色[J].《雕塑》,2008(6).
篇4
概述东西塔与瑞云塔的雕刻作品,分别代表了当时福建地区雕刻工艺的高超水平,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艺术风格。
1.东西塔及其雕刻概述:东西塔位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左右两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塔相距约200m。东塔名镇国塔(见图1),高48.27m;西塔名仁寿塔(见图2),高45.06m。西塔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228年)至嘉熙元年(1237年)间,为花岗石仿木八角形攒尖顶空心楼阁式建筑,塔身分为外壁、外走廊、内回廊、塔心柱等部分,层层收分,塔内中心为石砌八角形塔心柱,外为回廊,塔心以横梁、斗拱与塔的外墙相连结。东塔建造时间比西塔晚10年,建筑构造与西塔基本相同。东西塔从整体造型到营造结构设计缜密、工程浩大,反映了13世纪闽南乃至福建地区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东西塔每层嵌有佛教人物浮雕16尊,两塔共160尊,在须弥座上还有佛传图40幅、花卉鸟兽图48幅以及负塔侏儒16尊,这些雕刻使东西塔犹如一幅佛国的缩影,反映了佛教发展概况与佛教义理规制。虽然东西塔雕刻是南宋时期的作品,但由于泉州地处中国东南部,中原文化传入需一定的时间,因此文化发展速度较慢,所以还保留了部分唐代雕塑圆满、雄浑、大气的风格特征,同时又兼具宋代秀婉、细腻的特点。东西塔塔身雕刻的丰富与壮观在同时代我国其他古塔上是少见的。南宋时期,我国石窟造像艺术已接近尾声,所以东西塔雕刻可以认为是对我国佛教石雕艺术新的传承与发展。
2.瑞云塔及其雕刻概述:瑞云塔(见图3)始建于明万历34年(1606年),是福清人万历首辅叶向高之子符丞叶成学和知县凌汉聊募捐兴建,并由名匠李邦达负责设计与施工,最终于万历43年(1615年)完成,前后历经10年。瑞云塔建筑样式美观,造型挺拔,雕刻精湛,外观线条和谐,是典型的中国南方风格的楼阁式石塔,堪称明代石塔的瑰宝,1965年被公布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瑞云塔为仿木构楼阁式空心塔,平面正八角形,共7层,高34.6m,由基座、塔身、塔盖和塔刹等4部分组成,塔身外设走廊,每层有腰檐,外形力求仿木构造,突出斗拱、梁柱等各种构件的作用与特点,逐层略有收分,整体造型笔直,古朴典雅。瑞云塔塔身自下而上布满了400余幅精美的雕刻,有佛、菩萨、罗汉、高僧、金刚、飞天、力士、麒麟、狮、奔马、玉兔、鹿、猴、花卉、树木、山水等形象。瑞云塔不仅外壁雕满了浮雕,而且塔内也有雕刻,每层塔心室内均设有佛龛,左右两边雕有菩萨、罗汉等像,甚至在每层台阶通道的顶部还刻有观音造像,堪称明代石雕的精品。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艺术虽创造于不同时代,相距达350余年,但均代表了当时民间雕刻工艺的最高水平,作为塔,它们之间有不少相同点,但也有许多差异之处。
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的对比
由于东西塔是由僧人主持建造的,具有浓厚的佛教义理和妙胜的含义,其中东塔代表东方娑婆世界,西塔代表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东西塔的雕刻内容紧密结合佛教的主题思想。东塔雕刻以佛教修行的5种境界即五乘为标准,从第一层到第五层依次为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与佛乘,并按照人物之间“性类相近,相应对称”的关系,每两尊一对排列在塔门和佛龛两边,形成尊卑有序、层次分明的佛教人物图,表现了东方娑婆世界的佛教精神。西塔代表的极乐世界提倡众生平等,因此,人物排列没有东塔如此分明的等级次序,而是相互穿插,每一层均有佛、菩萨、罗汉和高僧像。瑞云塔是由当地官员倡议建造的,具有佛塔和风水塔的双重功能,因此,雕刻在内容和排列上比较自由,不仅有佛、菩萨、罗汉、僧人等人物,还出现了大量与佛教关系不大的雕刻题材。通过对比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题材的差异性,可以窥见古塔雕刻艺术演变的状况。
1.佛菩萨造像的对比
东塔的佛菩萨雕刻严格遵照五乘来排列,第四层与第五层分别代表菩萨乘与佛乘,因此,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宝华菩萨、地藏菩萨等均在第四层,而第五层则为圆佛、通佛、三藏佛,以及释迦牟尼佛。西塔代表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从二至五层,均有菩萨造像,如第二层的香积菩萨、妙音菩萨,第三层的无名菩萨,第四层的观世音菩萨、相信菩萨、光明菩萨、月光菩萨,以及第五层的清凉菩萨、宝昙华菩萨等。这些佛菩萨像都位于塔壁上,形象高大,刻画生动。瑞云塔佛菩萨像所处的位置相比东西塔较为隐蔽,如塔第一层塔壁除塔门外,其余七个面每一面塔壁佛龛上方有并列5尊结跏跌座的佛像,7面共35尊,但体量较小,动态统一,刻画简洁。二至七层塔壁外面,并没有佛菩萨像,只是在每层塔心室正中的佛龛内安放佛像,而只有第三层塔心室佛龛两边各有1尊普贤菩萨骑象雕像与文殊菩萨骑狮像。另外,每层通往上一层的石阶上方,分别雕有1小尊观世音菩萨像。总之,瑞云塔的佛菩萨造像相比其他雕刻数量少,体积较小,造型变化简单,均位于较次要的地方。可以看出,造塔者无意强调这些佛菩萨圣像,只起了点缀的作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东西塔雕刻十分突出佛菩萨形象的威严,而瑞云塔的佛菩萨像更像是其他雕刻的配景,这说明东西塔更加注重佛教意蕴的缔造与渲染,而瑞云塔的佛教气氛相对较弱。
2.高僧、罗汉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高僧、罗汉造像的位置是遵照佛教中的规范顺序排列的。东塔第二、三层分别是声闻乘和缘觉乘。因此高僧、罗汉等像均集中在这两层,其中,寒山、拾得、丰干、法显、玄奘、宝志、慧思、道宣以及布袋和尚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高僧都出现在第二层,代表他们的是声闻乘,而阿难、迦叶、普化、长眉、佛图澄、目连尊者等代表缘觉乘,均位于第三层。代表西方净土的西塔则各层塔壁都有高僧和罗汉形象,如第一层的普化和尚,第二层的寒山、拾得,第三层的目连尊者,第四层的唐三藏,第五层的香严大师,其中西塔第二层上的香积菩萨头戴七宝冠,项后有圆光,弯眉秀目,身穿天衣,脚踏莲花,左手执一只香炉,右手将檀香放入香炉里,而第三层的迦叶摩藤尊者圆光头顶,大耳穿环,面部丰满,身穿袈裟,左手施智慧印放胸前,右手执扇。东西塔的高僧、罗汉造型均较端庄严肃,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包含宗教意蕴。瑞云塔每层塔壁都有许多高僧、罗汉造像,数量比佛菩萨像更多,排列顺序较为自由。第一层塔壁佛龛两边,刻有2幅高僧、罗汉像,但面积都不大。第二层至第七层塔壁和佛龛两边的高僧、罗汉像是瑞云塔雕刻中较为突出的塑像,每尊高僧、罗汉像刻画得十分生动幽默,突出人物动态和表情,性格鲜明,特别是第四层塔壁的一幅罗汉穿鞋造像,滑稽有趣,塔的第二层至第五层佛龛上、下方,还有一些高僧、罗汉造像。这些高僧、罗汉的动态比较活跃,如第五层佛龛下的一幅浮雕,伏虎罗汉坐在老虎背上,而另一名僧人用双手抓住老虎的尾巴,似乎不舍罗汉离去,想留下他继续讲经说法,而在同一层的另一幅图中,一名高僧骑在马上,前有一名和尚牵着马绳,后还有一名和尚挑着扁担和行李,这幅图应该是描写西行取经的故事。第六层还有一幅高僧行脚图,中间2名僧人带着斗笠,双脚踩在云彩之上,左右两边各有一名侍者背着行李,显得风尘仆仆。这几幅雕刻作品充满了生活情趣,更像是将寻常百姓的生活形态加以提炼与夸张,人物动态有着世俗化印记。总体看来,东西塔高僧、罗汉造像颇为严肃,具有宗教神秘感和威严感,而瑞云塔高僧、罗汉从动态到表情都比较活泼,更加具有社会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趋向世俗化特征。
3.神将、金刚等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还有许多神将、金刚等造像。东塔第一层代表人天乘,因此神将和金刚像最多,如东、西、南、北方四大金刚神,还有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等四大天王,他们全都武士装束,威风凛凛,如东塔塔壁西北面的西方广目天王,武将打扮,头戴宝冠,大耳穿环,额上有净天眼,表情严肃,身披盔甲,彩带飞舞,狮蛮腰带,脚穿战袍,双手抱拳夹住金刚杵,而南方金刚神头戴宝冠,上身赤膊,锦带缠绕,面露怒相,手执金刚杵,赤脚套镯,具有古印度武将的风格特征。东西塔上的这些神将和金刚造像,作为护法神,全都孔武有力,威风八面,有着不可一世的气概,体现了佛教的崇高地位和宗教尊严。瑞云塔只有在每层塔门的两边立有神将形象,7个塔门共12尊,这些神将是瑞云塔雕刻中最高大的塑像,其中第一层塔门两边的神将,面含微笑、披坚执锐,神采奕奕,一手执剑,一手放在胸前,有着明代武将的衣着特征。比较东西塔与瑞云塔神将等的造型,瑞云塔神将显得温文尔雅,贴近百姓的生活,明显是借鉴当时武将的形象,远没有东西塔神将来得威武和严肃,而是有着文人的气质,更具亲和感。东西塔和瑞云塔须弥座八转角还有八尊负塔侏儒力士,他们都矮矮墩墩,几乎都是单腿跪地。两座塔的侏儒力士造型动态基本相同,只是东西塔侏儒力士的手脚更加粗壮。唯一明显不同的是,瑞云塔有两尊力士用手拿着海螺拼命地吹着,仿佛在用号令指挥其他力士们努力托住高大的石塔,而同样西塔也有力士在吹口哨,但只是把2个手指放在嘴里吹,逼真地反映了福清当地海边渔民自然悠闲的生活场景。东西塔里面的人物具有写实性特征,每个人物都反映了一个佛教故事,传递着深刻的佛教哲理,如童子求偈、青衣献花、忍辱仙人等佛本生故事,而瑞云塔的一些人物造像,少了几分宗教意味,却多了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情调,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情景。
4.动物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的动物造像基本处于配景位置。东塔须弥座上的佛传故事雕刻,包括佛本生故事、佛本行故事、佛教比喻故事等共40幅,由于故事的需要,往往会出现马、龙、象、兔、羊、猪、鸟、狮、蛇、鹿、虎、鼠等动物,但这些动物只是作为配景出现。可以看出,东西塔的动物除了双狮戏球和二龙抢珠中的狮子与龙等少数动物是瑞兽,其余的大都具有佛教故事中的比喻含义,如“三兽渡河”中的兔、马、象,只是用来比喻声闻、缘觉、如来三乘行法的深浅。“丘井狂象”里的大象是比喻人生无常,黑白双鼠比喻黑夜与白昼,四条毒蛇比喻地、水、火、风,而“薄荷示迹”中的猪则是菩萨为救度畜生道众生的化身。瑞云塔的动物形象有龙、凤凰、狮、麒麟、马、鹿、鹤、猴、兔、金翅鸟、喜鹊等,均为常见的瑞兽,具有吉祥的象征含义。塔雕中如麒麟嬉戏、双狮戏球、白马奔腾、麋鹿踏青等,无不体现造塔之人祈求幸福、平安的心理。麒麟作为神兽,来自天上;石狮是权力与威武的象征;马是雄壮、力量的象征,代表了民族生命力和进取精神;鹿是天庭瑶光星散开时生成的瑞兽,与神仙、仙鹤、灵芝、松柏在一起,布福增寿,保佑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昌盛繁荣,而且“鹿”与官员俸禄的“禄”同音,代表了永享禄寿,加官进爵,这也反映了倡建瑞云塔官员们浓厚的儒家思想。另外,鹤是长生不老的仙禽,在我国民俗中,鹤与长寿永生、羽化升仙、平安祥和等寓意相伴随,含有道学思想,而“猴”读音同“侯”,有封侯的含义。东西塔动物雕刻更多是作为配景,虽然也出现不少动物,但几乎都是出现在佛传故事,不是主要形象,而是蕴含深刻的佛教哲理内涵,宣传教义成分更浓;而瑞云塔的各种动物雕刻往往作为主体形象出现,编具祈福之意。与东西塔相比,瑞云塔上的这些瑞兽蕴意更为丰富,不仅含有某些佛教内涵,还兼具儒家、道教以及民间风俗的含义,赋有喜庆、吉祥的象征性,寄托了当时官民的美好希望。
5.植物、山水造像的对比
东西塔的植物与山水雕刻几乎也是作为主体雕刻的配景。东塔的40幅佛传故事中众多的植物和山水图像皆是为了衬托佛教故事,如“玉象剃塔”里的花卉、“雪山苦行”中的树根、“童子求偈”和“田主放鹦”中的树木、“萨诃朝塔”中的山石等,这些植物和山水遵照现实主义的风格,造型风格写实。相比较而言,西塔须弥座和踏道两旁象眼板上的花卉图案还算较明显,造型完整,但与整座石塔雕刻相比,也是处次要地位。瑞云塔的一些植物与山水却是作为主要形象来表现的。如第三、四层塔壁佛龛下方的大型莲花图像,工匠们改变了原有中国传统莲花纹样严谨的装饰特征,模仿国画的造型风格,以浪漫主义的曲线来表现,虽然西塔石阶踏道边也有类似的莲花图案,但画面比较拥挤,缺少瑞云塔莲花的灵动感。瑞云塔三层塔壁的兰花造型飘逸灵动,清雅潇洒,几瓣兰叶向左右伸展开来,显得雄健刚劲,花朵在绿叶间绽放,风韵清丽,幽香清远,显然借鉴了国画中的兰花图,婷婷袅袅非常可爱,令游客从中品味到毛笔一波三折的韵味,感叹古代艺人巧夺天工的技艺。在塔的同一层外壁上还有图案,开着硕大的花朵,姿态优美,在风中昂首挺胸立着,令人肃然起敬。瑞云塔第三、四两层上的假山造型也颇为奇特,表面纹理纵横,姿态奇特竣削,曲折圆润,通灵剔透,具有苏州园林中太湖石“瘦、皱、漏、透”的审美特征。塔上雕山石在许多塔中也有出现,但雕刻太湖石在我国古塔中却极其少见,在福建300余座古塔中也绝无仅有,颇具生活气息,反映了福清当地文人墨客向往抒情悠闲的生活情趣。总之,瑞云塔植物和山水形象比东西塔的更加飘逸,更具有明代文人画的风格特征。而东西塔的植物、山水形象只是佛教故事里的配景,并不代表宗教和哲学含义,相较之下,瑞云塔的山水植物所具有的文人气息与民风民俗特色,更多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福清地方文人士大夫和民众普遍的审美情趣。
东西塔与瑞云塔建造的不同历史背景
综上所述像,瑞云塔雕刻不同于东西塔,佛菩萨圣像明显减少,更贴近民间的罗汉、动物、植物、山水等造像和图案增多,且风格鲜明,集中地体现了福清民风、民情、民性。同样作为塔,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出现的这些异同点,究其因,与它们不同的建造背景有一定关系。
1.东西塔建造背景
我国佛教在隋唐是鼎盛时期,但由于唐末五代中原地区战乱,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中原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帝王们多热心佛教。宋代福建的佛教寺院数量为全国之冠,泉州佛教也呈上升趋势。据《泉州府志》记载:“泉当宋初,山川社稷不能具坛,而寺观之存者凡千百数”,此时是泉州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众多寺院和僧人们拥有巨大的财力,佛教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当时泉州地区寺院多达170多座。原本东西塔是在唐通年间和五代后梁贞明时建造的木塔,因被火烧毁,后又建成砖塔。到了1228年,僧自证先将西塔改建成石塔,之后,东塔也改用石材。建塔期间,虽然有官员与民众参与,但主要还是由僧人来主持与设计,如僧本洪、僧法权、僧天赐等都曾主持建塔工程,因此东西塔完全按照佛教的仪轨进行雕刻,故其更多地体现了佛教的思想与观念,极具佛学含义。另一方面,东西塔的建造,体现了泉州佛教最兴旺的黄金时期,表明当时佛教已深深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并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东西塔的建造,可以说是南宋泉州佛教极盛的标志。
2.瑞云塔建造背景
明代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缓慢,已经失去唐宋时期的繁荣,而且由于佛教与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此时的佛教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中,与民风民俗进一步协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由于当时风水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地区大量建造风水塔,较少有建如东西塔那样纯粹的大型佛塔,而瑞云塔建造的动因首要就是要建座风水塔。瑞云塔的建造,是为求得国家兴盛,人民富足,渴望改变风水,改善居住环境,宣扬儒家尊君孝道的思想,且还有“镇邪”之用[3]。瑞云塔是由一班福清当地儒生倡建的。儒生们热衷于科举取仕,求取功名,建造风水塔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因此,瑞云塔众多的雕刻,除了与佛教有关联的佛菩萨圣像、高僧、罗汉、莲花、狮子、龙凤、飞天、力士等外,还出现了许多与儒学、道学以及民俗有关的其他形象,如马、鹿、鹤、猴、兔、喜鹊等。瑞云塔雕刻艺术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思想与民俗特征,融合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包含了人的品格以及对人生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创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建筑作品,将神圣世界同现世生活联系起来,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和谐圆满的精神追求,体现了明代佛塔不断世俗化的文化特征。从瑞云塔的雕刻中可以体会到,它的造型样式与表现手法均已突破了佛教仪轨的制约,体现工匠们的创意思维,反映了佛塔中国化的特色。瑞云塔雕刻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理想的向往,也表明了建造者具备福建民间艺术海纳百川、接纳多种文化思想的胸怀,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现实的生活气息,尤其是把明代士大夫及民众的思想、情感、观念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东西塔与瑞云塔的雕刻艺术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多的不同之处。
古塔雕刻艺术演变的文化学意义
1.反映了福建古塔雕刻艺术的历史沿革
如果把福建古塔建造年代以元代为界限,比较元代之前的塔雕刻和元代之后的塔雕刻,就会发现许多古塔存在着类似于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之间的差异性。元代之前(包括元代)的塔,如唐大中2年(848年)的连江仙塔、五代闽国永隆3年(941年)的福州乌山崇妙保圣坚牢塔、五代的仙游天中万寿塔、北宋元丰5年(1082年)的涌泉寺千佛陶塔、北宋政和7年(1117年)的长乐三峰寺塔、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的福清龙江祝圣塔,元至元2年(1336年)的石狮六胜塔等,均是典型的佛塔,塔上的雕刻虽然已有某些世俗化倾向,但主要还是体现了佛教的教理。元代之后的塔,如明万历16年(1588年)的连江含光塔、明万历31年(1603年)的福清鳌江宝塔、明万历年间的莆田雁塔、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的马尾罗星塔、清道光11年(1831年)的永泰联圭塔等的雕刻,则有着明显的儒、释、道以及当地民风民俗文化特征。因此,通过比较东西塔和瑞云塔的雕刻艺术,就能窥见福建古塔雕刻艺术的演变历程,进而反映出中国古塔的演变过程。
2.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历程的演变
我国佛教文化在魏晋时期已初具规模,南北朝时趋于兴盛,至唐宋时期达到鼎盛。而宋代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佛教开始衰落,并逐步世俗化,佛教思想与民间信仰相互结合,成为明代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自此,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民族宗教,对社会心理和民族习俗都起了深刻的影响。可以发现,古塔雕刻内容是随着佛教文化发展的历程而演变,东西塔与瑞云塔雕刻题材的差异性,正反映了这种变化。
3.反映了中国不同时代人文思想追求与艺术取向
古塔雕刻题材的变化,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唐宋时期,佛塔还具有较为纯粹的佛教功能与佛学内涵。宋代以后,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禅宗得到快速发展,它所提倡的“平常心是道”的观念,使原本威严、神圣、高深的佛学逐渐进入普通、平常的世俗生活,淡化了佛教高不可攀的神秘气氛。随着佛教在我国不断地中国化与世俗化,也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儒学与道教学说的融合,佛塔以及雕刻已逐渐由单纯的佛教功能,演变成具有儒、释、道及民间传统思想观念的建筑了,表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世俗化的趋向。从泉州东西塔雕刻到福清瑞云塔雕刻题材的演变过程,也正是佛教日趋世俗化的过程,是中国既有的民族意识将佛教文化消融吸纳过程的一个侧面反映,体现了不同时代人文思想的追求,也决定了艺术的取向,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