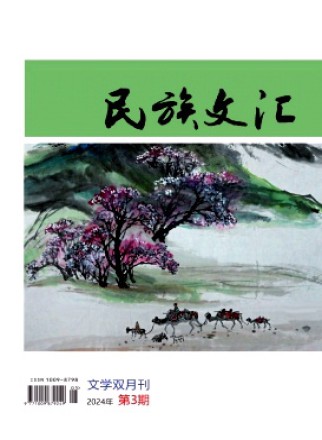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范文
时间:2023-11-23 10:02:07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少数民族文化是培养艺术人才的有效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是当前文化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实际中,其不但是对文化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所有院校所重视的教学资源和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指在艺术院校的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少数民族艺术文化是其构建少数民族艺术认知系统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风俗民情、语言行为,才能成为自有的知识,才可以深刻体会少数民族艺术,并时刻保持创作的热情,才可以自觉的对其加以传承行为。
教学资源,主要是指讲过学者的整理、耙梳,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能够进行典型代表的总结,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引入课堂,使其成为现代教育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校培养艺术人才的重要知识内容。
二、特色教材是少数民族文化变为人才培养资源的主要途径
在当前的社会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很多社会活动的主要资源。比如,宗教研究、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法学研究、社会文明研究、经济研究、生态研究等等。而作为艺术院校,特别是地方的艺术院校在教育资源研究方面的应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将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艺术教育资源的有效转化。
(一)进行积极的跟踪,即确保采风的经常化
在艺术院校中采风是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不论是从生活艺术创作源泉方面,还是从民间学习的意义上来说,采风都是必要和需要的。但是问题在于,采风不是在社会生活基层中进行生活素材的简单感受以及吸收,而是经过整理以后进行一定的艺术创作;同时更应该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进行人们的愿望、情感、表达方式的切实体验。这些内容是文艺创作在生活中进行灵感汲取的最重要内容。
(二)认真进行培植,确保研究的项目化
艺术院校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除了对各种对接渠道项目进行研究以外,针对自己学校实际情况,如办学设想、专业设置、学科布局等,设计出整体推进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的研究项目,作出发展和建设的理性分析、科学导引,这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是十分重要。把学校的研究项目和学生的个人爱好以及零星行为进行有效结合,将其引领到项目中去、引领到相关项目群体中去,还具有另外的意义,即通过项目研究进行精神的凝聚、队伍的锻炼、力量的整合、品牌的打造。
(三)积极加以支持,实现成果的课程化
成果课程化的研究,在本质上属于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研究中的办学行为加以焊接,是十分有效和有力的,其对于办学综合实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成果的课程化,需要有教材编写来进行有力的支撑。怎样才能把少数民族的艺术资源编写到现代教育行为中,使其成为教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对教学团体和教师进行考验的关键所在。在教学的实践中,应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提高的教师能力和水平,使其从一知半解的“知道者”成为真正的专家。
三、出版社应在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自觉意识和积极作为
篇2
一、邵阳蓝印花布纹样概述
1.多民族文化的影响
湖南邵阳建城于春秋时代,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名播湖湘。汉置昭陵,唐设邵州,宋称宝庆,民国改为邵阳。邵阳境内居民主要为汉族,元末明初,回族军人戍守宝庆,以后子孙繁衍定居其内银仙桥、九公桥、青草等地。近年,又因工作调入或婚入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壮族、侗族、高山族、彝族、藏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瑶族、土家族、傣族、黎族、水族、仡佬族等。全县41个乡镇,有35个乡镇居住有少数民族。邵阳自建城以来逐渐形成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文化,这样的文化涉及农民的吃、穿、住、行、用等所有领域,大都是以农耕民俗文化为背景,以吉祥寓意、意象造型、隐喻手段等体现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上。正是这些艺术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艺术影响和艺术的复合,并出现了一些混杂现象,这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种正常现象。其特征具有民族的传统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艺术风格质朴、纯真、强烈、绚丽、变化奇妙,充满了人生的爱恋和美好思想,蕴藏着深厚的民俗性、地域性和群体性。这些特征再加上邵阳自身的民俗观念及民俗意识,形成了独特的邵阳蓝印花布纹样。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也因此具有十分厚重的多民族文化底蕴。
2.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历史渊源
邵阳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降水集中,易遭干旱,光照充足,生长季节长。民国时期,境内种棉自给自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农业改进在湖南各县贷发和推广优质棉种,邵阳县作为当时全省五县棉作试验场之一,棉纺织业兴起,为邵阳蓝印花布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基础。
由于邵阳蓝印花布使用靛蓝单色印染,局限性很大,故而必须在蓝印花布的纹样变化上下功夫,让其显得素丽多样。蓝印花布纹样的题材和内容又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苗族的神话,在他们世代传唱的《苗族古歌》中,记录了从枫木图腾开始到蝴蝶妈妈生子然后从神到人、诞生了姜央,以及姜央在洪水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等故事。从植物到动物到神最后到人,反映出苗族人民对古代神话的理解和崇敬,隐藏了他们对深层次的生命的真诚追求及对生殖繁衍的渴望;二是源于邵阳的自然环境的写实和对民俗文化的写意表现。关于民俗,《管子·正世》中云:“料事物,察民俗。”《礼记·缁衣》中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载:“变民风,化民俗。”魏晋时阮籍《乐论》中将风俗释为“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邵阳丰富的自然物质资源为邵阳蓝印花布的纹样提供了很多素材。纹样大体可分为几何纹样、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及人物纹样四种,多用夸张、写意的形式表现。这一切都是结合邵阳民俗及民众心中对自然、生活、神话的体会,用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幸福、自由及对生活的热忱的追求。
3.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内涵
民间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说法,也有“出口要吉利,才能合心意”的要求。所以邵阳蓝印花布不仅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艺术价值,而且其纹样所选用的题材和内容都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吉祥纹样。“吉祥”二字,始见于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庄子》。其中有“虚空生眉,吉祥止止”一词。又如《说文解字》说:“吉,善也,从士口”;“祥,福也,从示羊声,一云善也。”邵阳人民主要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且集合了多民族的优秀精华,所以他们擅长用比喻、象征、谐音表意及特定的符号,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积极向上的心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体现邵阳人民的乐观自信、智慧和情趣,以及幸福和欢乐的气氛。
比喻。比喻是寓意的一种,是指人们在观察、揣摩过程中,由事象深入事理的结果,它除了表征事物的外在特征外,还包括诸如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戏文、典故等。例如由鲤鱼、龙门组成的鲤鱼跳龙门图形,《埤雅·释鱼》中说:“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清李元《蠕范·物体》中说:“鲤……黄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说明了这个飞跃的价值,后以“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或者用作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
象征。弗洛伊德说:“象征的表示就从来不是个体学习所得的,而可视为种族发展的遗物。”如费迪南德·莱森说,“中国人的象征语言,是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更有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邵阳蓝印花布纹样通过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花果草木或动物的纹样、色彩或功能等,来表达某些特定的吉祥含义或思想(图1)。《说鱼》一文中说:“‘莲’谐‘怜’声,这也是隐语的一种,莲喻女性或者是女性的生殖器官。”“鸟”即“鸳鸯”喻为男性。“鸳鸯戏莲”实质上说的就是男与女嬉戏,表达的是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和追求。
谐音。谐音本是文学中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民间俗称为“口彩”。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常用谐音的方式,将一幅图案组合表达出美满、吉祥的含义。“喜上眉梢”,“喜鹊”的“喜”直接通用,“眉梢”通“梅梢”(图2)。通过谐音就直接表达出了人们的喜悦、幸福、快乐及喜事临门的美好氛围。
特定的符号有两类符号纹样,一类是注重形式淡化表意的几何纹样,如鱼子、珠子、三瓣花、弧线、环纹、鱼鳞、太阳、月牙、波纹、绳纹、三角纹、锯齿纹、五角纹等,它们起着美化装饰画面的作用。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还有一类是民间千百年留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特定吉祥符号。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中也包含着这些特定的吉祥符号纹样,它们包括:方胜纹、万字文“卍”、盘长纹。这些纹样的主要内涵为:方胜纹,两个菱形压角相叠组成的纹样。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提到“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兮觌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图3);万字文即“卍”,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盘长纹,盘长俗称“八吉”,即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和盘长,盘长列为最末,但代表着佛门八宝的全体(图4)。
正因为这些符号具有这样丰富而吉祥美好的内涵,使得邵阳蓝印花布深受人民喜爱并得以广为流传。
二、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艺术特征分析
1.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艺术表现手法
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分为两种:一种是“匹料”,是连续纹样。其纹样组织形式有散点式的、缠花式的,还有常见的格子花,以几何形格子为主骨,当中填充散花组成纹样。可供人任意裁剪,缝制衣裳,或做被单、门帘等。另一种是“件料”,是适合纹样、专门用来做成被面、门帘、桌布、肚兜等特定形状的。“件料”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其基本结构为中心图案与边框图案组合而成。纹样的主题多为表现爱情,祈求平安、富贵、长寿等内容,由与之相关的单元纹样组成。“匹料”的图案组织方式有散花、缠枝花、格子花、满地花等形式。邵阳蓝印花布上散花、缠枝花、格子花、满地花图案组织,基本源于我国古代的织绣纹样,例如长沙西汉墓出土的织绣实物等,便可知其源远流长。
2.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艺术特征
邵阳蓝印花布构图粗犷大方,内容则细腻紧凑、浑厚朴实。因为邵阳蓝印花布是以油纸镂板然后刮浆漏印而成。因受其工艺的限制,为了防止花纹的脱落,构成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便是平面造型中的点、线、面。并且点、线的大小必须恰到好处,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太小的点,灰浆不容易附着;太大的点或线段,灰浆容易在染色时剥掉。这样的星星点点错落有致、极具韵律节奏的排列,就是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特色所在,它给人或粗犷强烈、或清新质朴、或精巧细致的感觉。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与其他地区相比,很注重用点来构成一幅蕴含吉祥和民俗观念的纹样图案。如蓝底白花的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就会要考虑白跟蓝两个颜色的面积关系。面积大的约定俗成被看作“底”,相反面积小的就被看作“图”。“图”与“底”之间会产生一种空间层次感和空间量感。邵阳蓝印花布则注重画面大效果,较多地运用大块蓝白、粗点、宽线来表现对象(图5“梅、兰、金鱼”,图6“凤穿牡丹”),布局大胆,巧妙穿插,飞翔的凤鸟与富态的牡丹相互映衬,从平稳中体现了有节奏的律动,使整个画面洋溢着富有生机活力的乡土气息。
三、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民俗意蕴
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民俗意蕴可以从生存、繁衍、圆满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生存即是求活,即指充满“生命活力”,活下来是最高的人生哲学,也是人生哲学的主题。为了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向往,邵阳人民在自己的艺术中高扬生命之帜,一切造型都被赋予了生命与活力。“活”,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活泼、洒脱。造型常常表现出造型手法的活泼和大气。数千年来深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劳动人民,长期挣扎于生活的最底层,他们仅仅想简单、朴素、踏踏实实地活着,所以生命、活力对邵阳蓝印花布纹样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繁衍。人丁兴旺、子孙延续都是勤劳朴实的邵阳劳动人民所祈求的。故而出现了许多符合这一愿望的纹样题材,如葡萄、葫芦、莲蓬、荚豆、石榴等多子植物,甚至老鼠等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都常被用来象征多子多福,像“老鼠偷葡萄”“老鼠偷南瓜”“老鼠偷白菜”等就成了吉祥纹样的主题来源。
圆满。中国人民深受古代太极阴阳哲学观念的影响,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人生宇宙观和时空观。反映在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布局上就是讲究圆满、完整,讲究对称、偶数,因其中蕴藏着平和、完美与吉祥的寓意。因此纹样多把成对成双的图案巧妙地相对置在一个圆形中,舒展自如,相反相成,互相照应又相映成趣,产生了一种积极协调又相互对立的运动感,这种格式被称作“喜相逢”。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之所以有独特的艺术特征,是与其多民族杂处文化交流影响、民俗观念、民俗意识密不可分的。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题材都是根据生活的需要和审美需要取材于大自然的动植物和人物自身,表达出人们对幸福日子的憧憬。同时它选用的纹样素材往往都会含有某种吉祥的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传统的民间风俗和人民的审美情趣等。邵阳蓝印花布纹样质朴,色彩清新,朴实无华,却是在多民族文化影响、融合下走出自己的特色的民俗艺术。
(注:本文为邵阳蓝印花布工艺技术及产业发展研究湖南省社科课题,项目编号:12YBA213)
参考文献:
[1]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2]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
[3]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中国蓝印花布馆.中国蓝印花布[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
篇3
(二)城市广场文化的特点
(1)城市广场文化与城市周围环境协调统一
城市文化广场与城市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统一,是构成城市广场文化质量的重要因素。城市广场文化一般都是开放型的,组成城市广场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周围的建筑,结合文化广场的主题,将其周围建筑科学合理地融入广场环境中。丰富广场空间的类型和层次,并完善其结构,有助于解决广场需求的多样性。
(2)城市广场文化共享城市空间
城市广场文化具有共享城市空间的特点,在共享空间里,人们扩大交流和合作,形成公共认识,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圣马可广场,它不但是威尼斯的市中心,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广场文化的代表作,人们把它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客厅。
(3)城市广场文化的标志象征
城市广场特色是城市具有的地方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民族在特定的城市和环境中的体现。广场的标志性建筑能带给人们文化休闲气息,广场特色体了当地人们的情趣和习俗。文化广场的设计要体现时代精神和风格,运用现代设计思想和方法,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追求新创意,使文化广场更具现代特征。
(4)城市广场文化亲民
演员同台献艺,不但声势浩大,还可以产生强大共鸣。平民化的开放式广场拉近城市广场文化多来自于群众,为民众喜闻乐见,是群众最有兴趣参加的文娱活动;民众与了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推进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5)城市广场文化形式多样、内容广泛
自娱自乐是城市广场文化的主要形式。随着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公民的自我保养、娱乐意识增强,多种自发的群众文艺活动应运而生。在居民小区等场所,早晚有许多民众健美、跳舞等。简言之,城市广场文化活动形式多样而且灵活,有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庆典、公益文艺演出,也有企业和商家组织的商业演出。有业余、通俗、普及文化艺术,又有专业、高雅、精品文化艺术;有传统和现代的舞蹈、戏剧和音乐,也有群众表演的民间艺术、乡风民俗、戏曲戏剧、书法,还可以是集邮、演讲、棋类、武术、广场交谊舞、广场民族舞、广场合唱等形式,可谓百花争艳。
(6)城市广场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企业及政府举办的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广场文艺演出,融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法制教育为一体。极大地展现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文化和精神风貌,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传承城市广场文化的措施
(1)完善城市广场规划和建设。合理规划城市广场位置和广场用地,重视城市广场规划的科学性及建筑的合理性,统一规划和建设商业广场、城市中心广场、城市文化广场、绿化广场、观景广场、纪念性广场。
(2)举办高水平文艺演出,打造城市广场文化氛围。广场文化是城市艺术文化推广的必然之路,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是重要的文化旅游推广活动,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以及文化、经济地位。
(3)利用城市广场开展文化教育和商业活动。广场不但是城市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开展的舞台,也是进行现代化教育的课堂。同时,城市广场文化寓教于娱乐之中,是群众自娱自乐、自我教育的良好载体。
二、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艺术
中国是具有灿烂文化、悠久历史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明大国。每一个民族的音乐舞蹈有其独特价值,风格、特点各异的民族艺术构成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艺术,民族文化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富含各民族的民族情感和习俗习惯。比如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火把节和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期间,都会在广场上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和演出,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不但增加了节日气氛、吸引了游客的参与,还增加了民族间的友谊和团结。
三、成都市广场文化是传承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成功模式
(一)成都市的地理与少数民族文化环境
(1)成都市的地理与文化环境
已有2300 多年历史的成都,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除云南外,四川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多的省份,其中拥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成都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少数民族不断迁居成都,各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在成都加速交流融和,成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国际大都市。随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频繁交往,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也随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对成都广场文化产生影响,并且逐渐成为成都市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通过广场文化得到保护,并在成都得到推广与普及。
(2)成都市节庆性广场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成都市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近年来节庆性的广场文化类型日益增多,尤以2007 年、2009 年和2011 年,成都举办的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最具代表性,它是成都最具影响力的节庆性广场文化活动之一。比如2007 年非遗节期间,在成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的广场,举行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展演,50 余场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与成都市民亲密接触,普及了成都市民对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了解,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对提高成都市民的文化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在非遗节期间全程观看了广场的演出,在四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演出的当天,现场座无虚席,成都市民更加熟悉藏族羌族和彝族的音乐舞蹈艺术,藏羌锅庄、彝族达体舞,羌族多声部组合演唱都成为了人们十分喜爱的节目,满足了群众的审美需求。在非遗节期间,公开出售首次发行的羌族多声部专辑《复音孤岛》,吸引许多群众的争相购买,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在广场文化的带动下,获得了新的展示平台和发展良机。在笔者的采访中,许多汉族群众十分欣赏和喜爱来自少数民族的歌舞,他们希望能够学习这些音乐和舞蹈,可见,成都广场文化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2009 年和2011 年的两次非遗节延续了第一届时的空前盛况,成都非遗节已成为全国性的四大文化节庆活动之一,成都推出了世界上首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大型文化节会。从2011 年第三届非遗节开始,这一国际文化品牌永久落户成都,成都成为非遗之都。第三届非遗节的各大活动更加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性,来自国内外的7000 多名代表,1900 多个非遗项目参加了本届非遗节。直接参与节会活动的人数达570 余万人,拉动各类消费61.5 亿元。正是大众的积极参与,让非遗焕发了青春,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在成都市和谐的民族氛围中广泛传播,众多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在这里交流互动,不仅扩大了其宣传,也促进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因此,成都市节庆性广场文化对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传承作用。
(3)成都社区性广场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成都市有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社区性广场,社区性广场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社区性广场文化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在成都市调查了多个有代表性的社区性广场,如成都市人民公园广场、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高升桥移动广场,此外还有一些居民小区的广场文化活动。在这些广场活动中,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所占的比重较大,虽然有众多不同的民族音乐舞蹈,但只要是形式喜闻乐见,易于传播,许多民众都愿意学习和表演。在笔者调查的社区性广场中,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藏羌锅庄是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代表作品之一。四川拥有中国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成都的地理位置与藏区、羌区紧邻,在成都居住着大量散居的藏族、羌族同胞,在成都市武侯区西南民族大学周边形成了稳定的藏族居住区和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附近的移动广场形成了藏族羌族音乐舞蹈文化的传播。藏羌锅庄是其中重要的传播内容,锅庄的表演自由灵活,凡喜庆佳节,广场文化多采用群众锅庄,藏羌锅庄的群众性和参与性很强,动作简单易学,音乐与舞蹈并举,具有藏羌文化的审美特点,气氛欢快热烈,符合广场文化大众性、公共性、平民化、审美性的需求,因此,锅庄成为了成都各社区和广场文化活动的宠儿。过去,仅在藏族羌族的农业生活中出现的藏羌锅庄,如今在成都市广场流行并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在现代化的成都大都市焕发出蓬勃生机。
此外,成都市社区和各个广场都会定期开展老年民族健身舞、交谊舞、吉特巴、三步彩的培训活动,这些舞蹈中有很多少数民族伴奏音乐,如《天路》、《飞向苗乡侗寨》等少数民族歌曲常常作为舞蹈音乐伴奏,成都市广场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完美结合,扩大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范围。
(二)成都市广场是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从当代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文化传播是需要以下四个必要条件。成都市的广场文化实现了这一传播过程,并具备文化传播的4 个必要条件。
(1)文化的共享性。藏羌锅庄是成都市民容易理解、喜爱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品种,藏羌文化的传播代表着成都其他民族与藏族、羌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共享。
(2)文化的传播关系。成都市民在广场中欣赏和学习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传播的渠道。
(3)文化的传播媒介。人类不但是文化传播者,又是最活跃的传播媒介。优秀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通过成都市民的热情参与而得到广泛传播,成都市民是最为活跃的传播媒介之一,成都的各类广场文化就是今天这个物的载体,同时也是另一重要的传播媒介。
(4)文化的传播方式。文化传播的方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模式,电视、广播、报纸都是其传播方式。文化广场这种传播方式是面对面,更加直接和真实的传播方式,成都市民在文化广场中欣赏和学习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亲身参与其中,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传播的真实性。
篇4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音乐文化被看成是各民族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的音乐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是这个民族智慧的象征。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其目的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音乐文化价值的同时,积极摄取其它民族音乐文化的长处,让我们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以鲜明的个性融入到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氛围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的西北部,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居多,并有回、瑶、侗、白等多民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孕育了当地原始、纯朴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湘西自治州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其音乐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与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意识息息相关的,隐含着深刻的内在情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产物,是当地人们自身生命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瑰宝。
然而,随着外来主流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音乐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一些珍贵的音乐文化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危险状态。湘西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面临着被冲击、渗透、同化的危险。面对这一现实,笔者认为,要尽快、有效的保护、传承这些富有特色的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学校音乐教育理应成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民间传承的重要补充,通过实施其音乐教育的文化功能,为少数民族音乐在当代的弘扬、创造、发展拓宽思路。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无意识的音乐教育行为(如宗教活动、民俗节日活动等)承担了传承与发展音乐文化的主要任务。但是,专业化的民族音乐教育伴随着世界音乐教育的正规化而出现,是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得以继续生存并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因此,如何实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功能,是当前乃至今后民族音乐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积淀
现行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主要是以西方音乐语言或音乐形态学的理论来进行建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审美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等构成了以“西方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而由于西方音乐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所处的文化深沉背景上的不同,在这种音乐教育体系中,必然会使少数民族音乐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被掩盖,不仅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也会使少数民族学生原有的价值观丧失,最终带来的是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所生成的文化积淀仅是针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灾难性后果。
多元的文化使得各民族相互学习交融,也使人们更加强调各自文化的民族化特征。作为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应将民族音乐纳入其中,给予其主体的地位,确立以民族音乐文化的积淀作为学校音乐教育根基的地位,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一种学科资源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音乐课程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对民族音乐保存、发展的目的。
二、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传递
由于少数民族音乐和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融为一体的结构特征和传承方式的口头特征,使我们无法从有很多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去认识、熟悉它。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文化传递都是靠其独特环境和历史传统相适应的方式进行的。在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中口传音乐的传递方式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口传音乐通常是一种非正规的、即兴的文化信息表达,它没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而是自然生成的,通过在与长辈、同伴、环境等诸多交流形式中进行的,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民族音乐传递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也与整个少数民族文化环境是相吻合的,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音乐固有的生存环境和传承方式随之受到相当大的冲击,给少数民族音乐在民间的自然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各少数民族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更多的与学校音乐教育结合在一起,借助学校教育这个平台,让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成为一种理性化、系统化的习得行为。
当然,实施学校音乐教育并不是以牺牲民族音乐文化的“原生态”为代价,恰恰相反,少数民族学校音乐教育应尽可能维护民族音乐的“正宗性”,将其文化中的精髓完整的传递下去,只不过传递方式可多样化,既可以是专业性的教学与研究,也可以深入到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语境中,进行非专业性的文化实践活动等等。
三、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相互交往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渗透、融合使各民族文化内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一次空前的全球化的文化整合正在悄然进行。正是在这种文化态势下,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却陷入了“自我中心论”的狭隘的价值观当中,“自我中心论”是一种以自我价值为最高价值,忽视、否定和排斥相关联事物价值,它与全球化的整体性、依存性相悖。这种缺乏世界眼光、排斥外来优秀的音乐文化、闭关自守、自我满足的文化价值观,必然会导致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停滞落后。
要解决上述存在的危机,唯有通过开放的、系统的当代音乐教育来完成,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既得天独厚的拥有当地民族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同时又能从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高度俯瞰这些资源。因此它能根据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势对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反思、审视,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一方面民族地区音乐教育不能简单采取“利用”和“发掘”的方式,而要把民族音乐已具有的独特个性和完整音乐素质的那部分音乐精华筛选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平等的音乐艺术来看待,才能使它们得到广泛的认同,比如:湘西苗族音乐的特点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加入一个“b3”音,“画龙点睛”的一个音恰恰展现了与其它民族音乐的不同之处。因此,教师要善于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民族的音乐特色,然后在结合听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获取音乐内在的节律和韵味,才能让学生理解这些“不准”或是“莫名其妙”的音响,达到一种心灵相通的境界。另一方面加强对异域音乐文化的交流、吸收。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方音乐理论体系,无论从完整性、规范性上来看,都是值得我国音乐教育借鉴、学习的。所以,对少数民族音乐不断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实现本土音乐与异域音乐的多元共存,将是今后民族地区音乐教育长期奋斗的目标。
四、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创新
在当今社会,少数民族音乐独特的文化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保存发展确实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但笔者始终认为,少数民族音乐在我们学校音乐教育中还只是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要改变这种现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强调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学校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进行创新的能力。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看到其传统音乐文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极为保守的“博物馆”式文化予以保存,这样其艺术价值不仅得不到有效的传承,也会让它落入“原始”、“落后”的境地。保护确实责任重大,但创新才是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比如:吉首大学舞蹈专业的教学正是不断的从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风俗礼仪、传统节日、服饰特色中提取舞蹈元素,大胆地对民间音乐文化加以创新,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舞蹈作品,如《猴儿鼓》、《扯、扯、扯》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民间音乐文化对于前人是一种创造、一份承载,而对民族地区音乐教育则是一种资源、一种延续,这种延续不是简单“保留”、“维持”,而是一种不断赋予民族音乐文化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的过程,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改造更新的过程。总之,唯有利用民族音乐教育推动族音乐文化的创新,才能使之艺术长河生生不息,永远流淌。
如上所述,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学校教育,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音乐教育理应承担起传承地方音乐文化的重任,这既是它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使命,也是它立足和发展的需要。正如著名的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所说:“通过生活本身,传统将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从人民生活中被抹去,企图阻止这一点,就等于阻拦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是徒劳无功的。现在,接受传统、保持传统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积极的部分,这是受过教育阶层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军.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